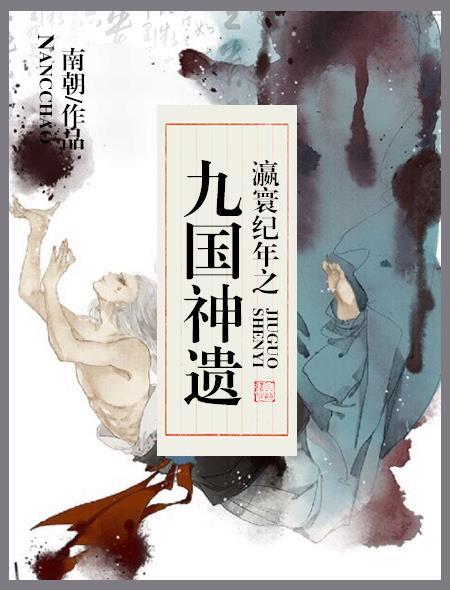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公主是尊菩萨(重生) 作者·圭先生 > 第102页(第1页)
第102页(第1页)
一听要重新接骨,李凌冰整个人都傻了。要知道十月一十六日,定州城内。丹橘给李凌冰端来荠菜豆腐羹,将?盛汤的大勺子递到她嘴边,见?她不张口,急忙道:“夫人,不烫的,我替你尝过了。”李凌冰奋力把身子支起来,悬腿向后荡,沉一口气,终于把自己摆成一个舒服姿势,挑眉问:“你怎么尝的?丹橘戳戳桌案上的小勺子,“用勺子啊!吃汤不用勺子,还能用什么?”李凌冰有点想念小霜。她叹一口气,把碗和勺子接过来,贴着羹面刮下薄薄一层,将?比脸还大的汤勺放到嘴边,吹凉了,送到嘴里,咬了一嘴的瓷器,吸水一般吸羹水。丹橘叉腰摇晃身子,最后蹲在地上,抱膝仰望李凌冰,“夫人,君侯好像挺节省的,给你的吃食里都舍不得多放几根肉丝。”李凌冰神色凝重,特意挑了一根肉丝嚼,这一点荤她都要适应很久。唉,还是有点腥。她像个垂垂老矣的人,只能克化肉沫星子。李凌冰问:“丹橘,你做侍女前,是做什么的?”丹橘眨眨眼,“帮我爹揉面做饼的。”李凌冰顿时?噎住,一个劲咳嗽,把碗勺放下,朝丹橘伸手,朝她空抓几下,任凭她怎么暗示,都没有把丹橘唤来,只得提醒她:“给我手帕。”丹橘弹起来,给李凌冰递手帕。李凌冰边擦嘴角,边苦笑?问:“想家吗?做侍女虽然清闲,却不自由。”丹橘眼神暗下去,“不想。”李凌冰问:“为什么?”丹橘别过身,悄悄抹一把脸,转回来,含着眼泪笑?道:“家里人都死没了,难道只想那间破屋子吗?”李凌冰迟疑问:“他们……怎么没的?”丹橘回答:“打仗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落下来的火石,房子塌了,除了我,都被压在房梁底下。挖出?来的时?候,我都认不出?哪个是爹,哪个是娘。”李凌冰说?:“我给你多多的钱,把家人好好安葬吧。”丹橘急忙摇头,“早就有人给过我钱了。君侯把死去的人一起葬在城外的地里。我的家人也在那里,我时?不时?就可以?去和他们说?一会儿话?。他还让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来大房子里找活干。他说?,要找个力气大、心地好、人又机灵可靠的人服侍他家夫人。君侯挑中了我。夫人,你和君侯都是好人,我会好好伺候你的。”李凌冰淡笑?,继续慢慢喝汤羹。丹橘说?:“他们都说?,要是没有君侯,定州城早就被水淹了,大家早就死了。”李凌冰道:“嗯,他们说?的没错。”丹橘问:“夫人,君侯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走了有十多天了吧。”“十一天。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李凌冰看着丹橘,笑?道,“不过没关?系。君侯不在,我会照看你的,丹橘。”十一月初九日,北境虎牢山阳,夜。严克和高晴围坐在篝火边分饼吃。一黑一白?两匹马正在旁边低头吃草料。高晴咬一口干饼子,猛嚼几口,仰头过一口水,拔长?脖子往下咽,转头问严克:“四公子,你送了我一路,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再送下去,就到北境了!”严克盯着手中的半块饼,一言不发。高晴用脚刨一下地,狠狠咬饼,腮帮子鼓囊起来,撇头嘟囔:“想见?家主就直说?,还借我的名?义送人。送了那么久,天边都走到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干都干了,哪用得着你现在负荆请罪!”话?虽这么说?,高晴心里也有种做错事,等着挨父母胖揍的不踏实——他自己也犯怂。严克抬眸,高喊一声:“高雪霁!”高晴眼皮一翻,“干嘛?”严克把酒囊丢过去,“喝酒,闭上你的嘴。”高晴“切”一声,用嘴拔掉酒囊的盖子,仰头“咕嘟嘟”喝酒。严克望着火堆,火苗在他黑眸里越蹿越高,他问:“高雪霁,你跟在父亲的身边日子久,父亲平日里是怎么说?我的?”高晴只管一个劲喝酒,眼皮向下垂。严克苦笑?,“明白?了,父亲他从来没提起过我这个儿子。”高晴双臂撑地,仰头道:“他是主帅,要关?心全军的兵士。他是长?辈,要训诫我们这群皮猴。他是个大忙人,很少会为一个人停留太久。我敬他为父,亲你兄为兄。大家同在军中,除了商议军情,很少聊私事。我难得和家主说?上话?。我和那群兵没什么两样,一样得从人堆里,抬头仰望北境之帅。”他盯着严克,“不过,我还是要说?,你父亲是我平生见?过最好的人,一个真真正正的大英雄。”严克盯着篝火发怔,然后,他仰头,盯着黑洞洞阴沉沉的虎牢雪山,又一次陷入沉默。他父亲犹如?这沉默不言的高山,生来就是让人仰望的。寂静的夜响起“咔嚓”一声响——哪里的雪裂开了,然后,轰隆隆响起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