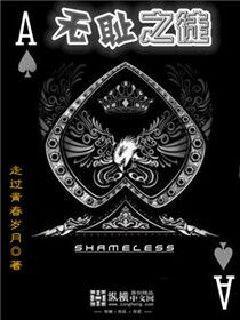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梦见明星住在隔壁 > 第32页(第1页)
第32页(第1页)
“不是。”言文作顿了一会t?儿,“是在墓园里。那天我看见你了,但你应该没看见我。”“原来是这样。我去墓园的机会少,我就想陪我妈妈多待一会儿,所以一般也不关注周围的情况。”“对不起,勾起你的伤心事了。”“没事。”林亟书将头埋起来,转了转那枚戒指,“既然你都偷偷戴了,怎么不干脆戴无名指?”“你还没同意。”言文作那可怜兮兮的声音又冒了出来,说完还恰到好处地叹了一口气。“那等把原来那枚戒指找回来,言先生再给我戴上吧,戴无名指。”林亟书安心地窝进了言文作怀里,让晴天彻底变成阴天。信与不信,活猫死猫,都无所谓了,薛定谔的猫是死是活她不在乎,只要她林亟书的猫活着,他们就可以继续走下去。言文作心满意足地抱紧了林亟书,“再睡一会儿吧亟书,中午助理会过来,他手里有些东西,你肯定会感兴趣。”等到林亟书坐上文心的车时,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点。文心主动要求当了今天的特邀嘉宾,要去给林亟书撑场面。“我只是去找粱姿其对质而已,你不是非要来的。”林亟书递过去一个保温杯,看着因醉酒而颓靡的文心摇了摇头。“保温杯?不是吧你。”文心头痛不已地揉着眉心的位置,还不忘吐槽,“言文作把老人味过给你了?你不如拿个暖水瓶来算了。”“不喝?那这醒酒茶我就拿去倒了。”林亟书已经掌握了对付文心的诀窍。“我只是嫌弃,没说不喝。”文心撅着嘴抢过保温杯,连喝几口才停下,“没想到你酒量居然这么好,亏我一开始还怕你真的晕在洗手间里。你说你还蛮大胆的,万一粱姿其想杀人灭口呢?”“哪有这么夸张,卢年占杀人她都不可能杀人。”林亟书无奈地瞥了文心一眼,想起一件要紧事来,“我走的时候看见你跟着一个男人,那是你男朋友吗?”“哎呀,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你要去找粱姿其对质是吧。”文心生硬地转移着话题,“你准备怎么对质啊?”“对她有话直说就行,我要对付的人是卢年占,不是她。把利害关系都说清楚,如果她聪明的话,她就知道应该站在哪一边。”林亟书将文心手里的保温杯收了回来,又把左手的戒指摘下套到文心手上,“再保管一下吧。”“哎呀,丢就丢了呗,都说他那箱子里有一堆了。对了,你当时怎么确定粱姿其一定会把戒指偷走的?”“她从小就喜欢抢我的东西,她受不了我过得比她好,更重要的是,她肯定接受不了别人说她的戒指是假的。”“而且,”林亟书想起酒会上言文作的演技,“前夫的身份不再是秘密,他们敲诈的筹码没了,总得想点别的办法才行。”车子停在了巷口的位置,林亟书还没下来就已经达到了吸引注意力的目的。文心特意选了最扎眼的一辆车,粉色的车身上镶着水晶,立刻把梁家的两位八卦王勾了出来。“真不用我下去?”文心从后座探出头来,拉住下车的林亟书。“不用,你等我一下就行。”林亟书将座位上的文件袋拿起来,她想起中午助理送来时的情形,当时她觉得助理未免太过拼命,不仅要辅助言文作的工作,还得替他去盯人。不过在了解到助理那让人瞠目结舌的高工资后,她也稍微理解了一点。助理本身和言文作是一路人,都是工作狂,高工资至少能让他的剩余价值得到一些回报。她抱着文件袋,直接走进了身后的房子,“梁阿姨,梁叔叔,我找姿其。”“找姿其?”梁晚把看车的的眼神收回来,“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啊,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林亟书将身后的门关上,“我也是为她着想,有些话在别的地方不好说,还是在自家说对她比较好。所以,麻烦你们叫她回来一趟吧,就说我找她。”梁晚和梁长军面面相觑,还是梁长军先打破了尴尬,走到一边给粱姿其打去了电话,他的主动倒是让林亟书有些意外。茶和点心被摆到了桌上,这是小时候林亟书常常能吃到的东西。当然,是在她妈妈死之前,和梁晚关系还很好的时候。梁晚热情地招呼林亟书坐下,“亟书啊,小时候你最喜欢来阿姨这里玩了,你和姿其关系最好,长大了也不例外嘛,以后没事也多来玩。”“谢谢阿姨。”林亟书端起茶杯,让右手上的小钻戒入了梁晚的眼。“这是订婚戒指?怎么戴在右手啊,阿姨没见识,但是看着有些小气哦,听说你未婚夫很有钱,家里在承州也是数一数二,怎么买个这样的戒指呢?”茶有些烫,茶杯被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林亟书捂住右手那枚戒指,露出一丝轻微的尴尬,让梁晚产生了和粱姿其一样的误解。“唉,阿姨就随口一说,你别放在心上。现在都讲究门当户对嘛,我们毕竟是小巷子里出来的,人家也不好太抬举。这样一想啊,我们姿其还是走运些,虽然男方没有你未婚夫那么有钱,还结过婚,但在他家在隔壁市算是很不错的,还给她买了这么大一个戒指。”“阿姨,右手上这个不是我的订婚戒指。”“你左手没戴东西啊?那你的戒指呢?”茶终于晾凉了一些,林亟书端起来尝了尝,随后才慢条斯理地开口,“被姿其偷走了。”“什么?”梁晚还带着笑意,像是没听见似的。“我说,我的订婚戒指被姿其偷走了。”林亟书特意放慢了语速,看着梁晚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变化,比起困惑,她脸上的恐慌更多一些。“误会了,这一定是”林亟书将手搁在茶杯的沿口,轻轻敲了敲,那茶杯上有个小小的豁口,她觉得梁家那虚假的体面都从这里裂开,倾泻而出。“梁阿姨,当年我妈妈把自己的戒指给了你,帮你解决了经济危机。到了现在,如果姿其有什么困难,我也不是不肯帮忙,只是她不能直接偷吧。”:他坐牢也没关系,你呢?从某种程度上,梁晚和粱姿其这对母女真的很像,甚至比林亟书和妈妈还要像。她们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演起戏来,言文作都甘拜下风。按照林亟书对她们的了解,只要面子上没有完全撕破,那里子里的东西就都还有隐藏的余地,就像如果她没有在饭局和酒会上戳穿一切,粱姿其一定还会接着演。此时此刻,梁晚不甘示弱,她嘴角含笑,眉毛却拧着,“你这孩子,乱讲什么呢,阿姨虽然性格好,总是宽容你,你也不能这么没礼貌啊。”这样虚假的话林亟书听过多次,从前她习惯忍耐,再不舒服也只会内耗,向内进行自我攻击,现在她才察觉到,原来这些话这么难听,忍耐起来这么痛苦。“当时妈妈走了,她手上戒指不见了,是阿姨你主动来告诉我,说妈妈临走前担心你家的债还不了,特意把戒指给你,好卖点钱贴补一下,不是吗?”“你看你”梁晚将茶壶拿在手里,起身去添热水,“陈年往事了都,我当时告诉你都是为了你好啊,你妈妈那么善良,我得让你知道她的善行嘛。你说过了这么久了,你现在拿出来讲,是想向阿姨讨债?”“我要是想讨债就不会等到现在了。”“是嘛,就说你是个好孩子。”梁晚添了水回来,又把点心往林亟书那里送,“你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阿姨总是备着。”“阿姨,我不是想把妈妈的戒指要回来,但我得把姿其偷走的戒指要回来。”“林亟书!”梁晚终于黑了脸,将那碟点心重重的一放,“由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你今天不打一声招呼跑到家里来,胡言乱语,一下说姿其偷东西,一下说你妈妈的戒指,你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