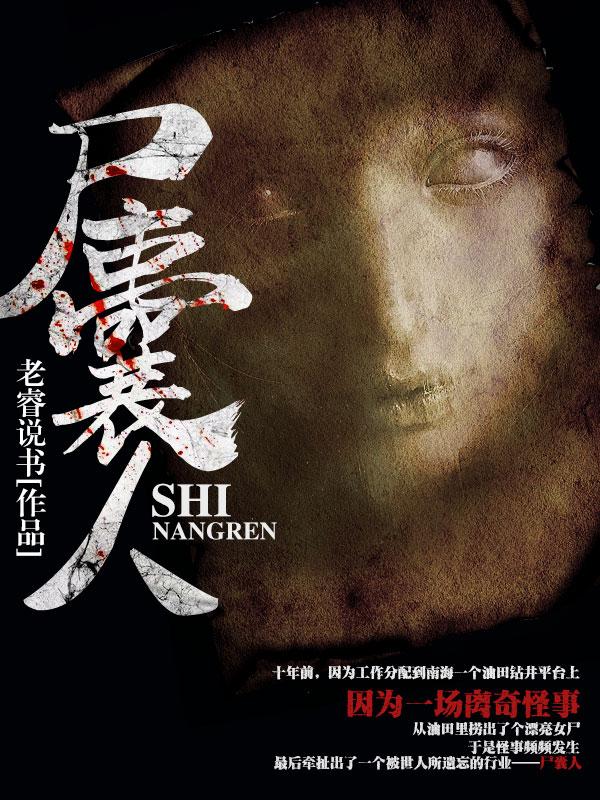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盛京小仵作免费阅读 > 第289章 曲终散(第1页)
第289章 曲终散(第1页)
广袖揽月,星火如豆。
比之外面亮如昼,房间内漆黑幽暗,静谧无声。
木门推开的‘吱呀’声音被放大,打破了一室的黑暗与幽静。
兴王妃在窗边坐了许久,侧面对着外,月光照身上,脸庞像是罩了一层寒霜,真成了冰美人。
发髻被重新打理过,一丝不苟的盘好插上一根点翠孔雀簪,衣服也换过一套,凤仙大袖鎏金炮,万分雍容。
她坐在那里,从妆容到坐姿,没有一处能让人找出不合规矩,简直是拓印在画上的仕女图。
皇帝负手迈步进来,王且点上灯,橙色火苗跳在兴王妃眉眼间,她眼神动了动,缓慢起身如平日般仪态端正的行礼,“臣妾参见皇上,皇上万安。”
皇帝冷冷的看他一眼,转身坐下,讥诮道:“好一个万安,江氏,你毒害朕的胞弟和侄女,你还让朕万安。”
兴王妃敛眉垂眸,“败者为寇,臣妾无话可说。”
“荒唐可笑。”皇帝当真冷笑出声,“你这话说出来,似乎兴王府屈就你了,近二十年夫妻,你就把兴王府当做你权势的争夺地。”
兴王妃弯了弯唇,眼神冰冷道:“是啊,近二十年臣妾便是困在这方寸之地,看得最远的地方,莫过于头顶这片天空。臣妾一直有个疑问,同样身为人,为何女人天生就该待在后院,成日里为几两碎银吃穿用度汲汲营营,外面天地广阔,怎么没有我们一席之地?”
皇帝冷漠道:“朕可不是来听你这番谬论,朕问你,你处心积虑做这些,是为了让你儿子上位,名正言顺继承兴王府,他在哪里?”
“他死了。”兴王妃偏过头看向闪烁的灯火,神情木然道:“否则我为什么要害死子桑归,因为他已经没有了用处。”这句话说的格外无情。
“他是谁?”
“皇上来之前,想必已经把所有事情都查清楚了。恐怕也知道了我和智灯的过往,那我也不需要隐瞒了,和我有私情的是智灯,慧能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已经死了。”
兴王妃平静的语气中带着点疯狂,火光在眼底涌动透出一抹殷红,“王爷发现后杀了我的孩子,我要替我的孩子报仇,这有什么不对?”
皇帝冰冷的目光如刀片,“所以你让血脉相连的两个孩子自相残杀。”
“残忍吗?”兴王妃嗤笑:“人生来有罪,这世上没有一个无辜者,皇上应该比我更明白,骨肉不过如此,讲什么怜悯同情。”
“虎毒不食子,你连自己女儿都不放过,枉为人母。”皇帝厌倦了和她继续对话,抬手一挥,王且弓腰走过来。
明黄色的龙袍在兴王妃眼角余光中翩然离去,桌上多了一个小瓷瓶。
王且手握着拂尘低声说道:“王妃,请今夜上路。”
关上门,里面再次恢复死寂。
不知何时,兴王妃走过去将小瓷瓶放在手里,脑海里浮浮沉沉,所有过去一切如走马观花迅速回忆一遍。
还没有成为兴王妃时,江婉真也曾年少糊涂,喜欢上年轻英俊的儿郎,不过她很快发现情爱实在无趣,只是长久空虚寂寞岁月中一点聊以慰藉。
后来站的高了,她又想,当初文承在战火纷飞里将四分五裂的国家一统,谁敢说一句女人不行?只不过是那些男人做惯了高高在上的姿态,不愿意屈居于女人手下。论谋略轮手段,女人哪一点比男人差?
差就差在生不逢时,没有给她大展身手的天下。
当一个花瓶般摆设的王妃已经够让她憋闷,这种压抑在江婉真知道兴王在外还有一个私生子并用过继的幌子把私生子接回来时达到顶峰。
她想起了她的儿子,既然子桑归可以,为什么她的儿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