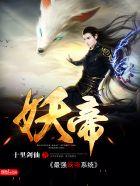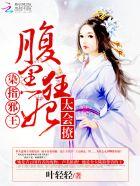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意思 > 6 第六章(第2页)
6 第六章(第2页)
宋照岄在心里默念着,第十一日。
夜里北风如同野兽哭号,更漏声隐在心跳里,偶有不识趣的风撞了门窗,宋照岄都恍惚是季息回来了,扯了床帘喊绾风去探。可城门紧闭,烽火台的星火只照见霏霏雨雪。
季息走时河面上冰且薄薄一层,畜牲不觉踩上去就裂开冰纹,宋照岄今早去看新到的粮草,运粮车就已弃了桥,大队直从冰面上来。
才是宋照岄几轮心悸的工夫,天就入了冬。
季息可好?宋照岄只恨回绝了石隽养鹰的想法,思绪如杂草丛生,一天天的焦急越垒越高,哪怕能寄一封信也好,记挂能从心里稍微吐出去些,她就要被压垮了。一丝边关的声响都像火苗,从心口一路烧到嘴边,恨不得从口里生出火焰,照亮他回来的路。
可军中用于联络战情的鹰已待命了三日,了无音讯,连个去处都找不到。
好在季息最终还是平安归来,宋照岄悬着的心终能放下。
朔州之战中,季息本想抓住时机进一步追击,却发现送来的粮草有问题,只得暂缓出兵。
年节时,二人互表心迹及真实身份,制定后续回京计划。
季息回城后,以通敌的罪名杀掉了除郑禹衡外的郑家幕僚和侍从,试探郑禹衡是否知道此事,在确认其懵然不知后,与宋照岄谋划借郑禹衡和况方回京汇报之机回京的事宜。
回京这一路凶险,到京城方能以真实身份示人,因此二人想假借护送兵卫的身份,使季息偷藏其中。
其后季息伪装伤重,无法上京,郑禹衡说动宋照岄以侍妾之名随他回京,而石隽和袁鸣宇作为边将代表跟随回京,季息本想混在兵卫中一同回京,但回程路上,将领兵卫入夜时与郑禹衡况方不住同一个院子,而郑禹衡对宋照岄之心令季息无法安心自处,怕郑路上行不轨之事,季息只得混入况方的侍从中。
在回京途中,二人才终是讲明季息身世和姜家一脉的情形。
季息,原名赵承玦,是皇帝第四子,因此以季为姓,母亲为皇后身边的婢女,名为沐溪,因而在外时以季息为名。小时候在宫中住处为韬光阁,意为美玉韬光,玟璇隐曜,美玉韬光。
虽然从小在宫中长大,可姜皇后事务繁忙,虽然择了宫人管教,但不能日日亲自看顾,皇子们寝殿都在宫中东北角,为了在宫中不惹人在意,怕他人发现皇后对他着意看顾,因而并不能在照拂宫中诸子之外,额外照顾于他。又怜惜他小小年纪,母妃已逝,所以每五或十日都会召他近前,或诊身子实虚或问功课,但宫人们惯会作假,赵承玦年幼时,便只在见皇后时特意照顾打扮,平时虽也大致做事,总不尽责。
这种环境下养成了季息后来的性格,老谋深算,习惯走一步看十步,但出击时则一击必中,未决定时思前想后,细细密密逐条谋算,但一旦决定,则一往无前,九死不悔,如烈火飞箭,炽烈炫目。
他面对朝事和父皇,只能韬光养晦,避让贵妃和赵承环,但内心压抑着愤怒和失望,把这些暴劣的情绪都在战场上释放。
此外,在宫中因为生母身份低微,又年幼失恃,不仅赵承环有意无意欺侮他,宫中稍得势些妃嫔的子女亦不把他放在眼里,唯有姜怀音和偶尔进宫的宋照岄对他和颜悦色。
姜怀音自幼长在宫中,见惯了人们拜高踩低,兼之身份敏感,不便多事,而宋照岄幼时则大胆赤诚,仅有的几次见面,均把他当作一般的皇子玩伴,既不刻意迎合,亦不嘲弄贬低,不仅在赵承环面前替他出头,还惦记着不经意间说出口的小约定,在再入宫时主动找他。
而姜家本为开国勋贵,两代之后,当时的老姜大人垂垂老矣,而小姜大人又在太学中才名惊艳,《定边策》一出,更是朝中人人争相结交,皇帝一方面担忧姜家在朝野中的影响力从老姜直接传给小姜,另一方面又对姜维桢的才学很是欣赏,不忍明珠蒙尘。
因而,待内阁初定定边策,选西北边陲为试点后,皇帝就派去姜维桢西北作督军,推行新政的同时削弱姜家在朝野文人中的影响力。
姜维桢在边军整顿军务,改制军制,教化外民,镇压哗变,乃至开设边贸,施行诸多举措,皇帝由初始的欣喜变为忌惮,又将姜维桢召回京,暂令无实权的职务。
待到皇上准备为皇子选妃,姜家一有边军支持,二在朝中亲朋故旧甚多,三被圣上冷落许久,为了拉拢姜家,更让姜家站在未来储君这边,将姜家长女先后许配给齐王和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