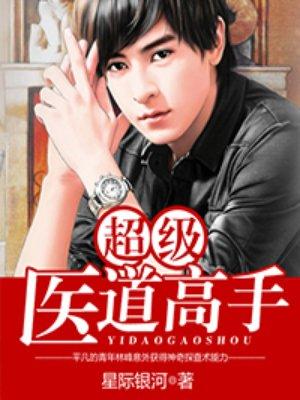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绯宇剑星 > 第100页(第1页)
第100页(第1页)
只要往深了想,苏玲心中就会涌现无数可怕的画面。其中的一些画面,甚至在很久以前就在她的脑海中上演过,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在那样司空见惯的夜。但她坚信苏朝晖还活着。两个月前,她接到那通电话,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声妈,但她无比确信这就是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这通电话,让她撑到现在。敲门声还在继续。这段时间,街坊邻里都对她温声细语,她表面上神色如常,其实是靠着无尽的忙碌与安眠药换来的。苏玲扶着床沿,挣扎半天,勉强站起身来。她披上衣服,颤巍巍往客厅走,摸到了防盗门把手,却连看猫眼的勇气都没有。人能承受的痛苦是有极限的,这根弦在苏玲脑中绷了三个月,日夜煎熬,度日如年,已经到了极限的极限。一门之隔,却如重城。透过坚硬的门,她仿佛看见了门外的世界,那里站着恶兽,它凶残,邪恶,躯体庞大如山岳,散发着腥咸黏腻的血腥;那里站着神色沉重的民警,他递上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它那么轻,那么小。苏朝晖刚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轻,这么小。脑中嗡的一声。有东西断了。“啊!!!!”苏玲尖叫着瘫坐在地,“你别敲了!”她开始语无伦次地哭喊,同时捂起耳朵,试图掩盖一切的声音,“别敲了!!求求你不要再敲了!!”“阿姨!快开门啊!朝晖哥哥回来了!”门外的顾晓波听着那尖厉的惊叫,早已吓的脸色发白,她仍执着地砸门,一边砸一边哭,她不知自己为什么哭,也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在这一刻,她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儿童天性里的纯粹,让她对大喜大悲感同身受。手拍疼了,她蹲下来揉手,又推推门边的苏朝晖,只觉得他浑身都是尖锐的骨头,硌得手更疼了。她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睡到这种程度,拳打脚踢也不醒。从光明到淮陵,将近六百公里。苏朝晖与宋宇分别后,直奔当地的客运站。他手头的钱不多,也没身份证,只能坐有限的几种大巴,而且没有直达,还要倒几次车。当时是早上四点半,他上了第一趟车,车里很安静,大多数人都因赶早而昏昏欲睡。这趟车要坐五个小时,他又困又累,坐在最后一排。他第一次独自坐长途,十分生疏,不敢睡死,将袖口拴在座位的把手上,一来是怕坐过头,二来是心中有创伤,对一切都感到怀疑,难以信任外界,总担心再给拐走,只听自己的直觉。旁边坐着个中年女人,苏朝晖在困的快要昏死的时候,曾试图跟对方交代,让她到站喊醒自己,但那妇女口音非常重,她叽里咕噜说了半天,自己根本听不懂,只好一路掐大腿强撑不睡,终于熬到第二站。第二站是两省交界处,乘客南来北往,务工者居多。走南闯北的人健谈,车厢里比上一段热闹。等车的时候,天空开始下雨,雨点子不大,也不冷,有泥土的芬芳,很清爽。越是往南,水汽就越足。苏朝晖也就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上车后,他的邻座是个沿海口音的黄毛男孩。也许是那一带人的长相和语气都有显著的共同点,苏朝晖觉得他很像兴旺,就与他攀谈。男孩比较开朗,说自己在厂里做毛绒玩具,说最近回家休息,还拿烧卖分给身旁几人吃。苏朝晖毫无胃口,他听着周围乘客聊天,又开始困的发懵,索性睡得不死,到站时被男孩叫醒。在这几段路途中,苏朝晖好几次想给苏玲打个电话,报平安,但最后都没打,因为一切都没有自己活生生出现在她眼前更显得平安。苏朝晖经历了三十多个小时,终于在这天上午到了淮陵市。当时天擦黑,他从汽车站出来的时候,首先看见的是路边升腾的白色蒸汽,那是他最爱的乌粢饭团,他直奔摊头买了两个,各加了两根油条,米几乎包不住馅。蹲在摊边,他边吃边哭,无法停止。他不知道是眼泪咸,还是饭团咸,他发誓,他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团。偶尔抬起头,他看见车站人头攒动,马路川流不息,听见自行车铃声清亮,淮陵方言坚硬爽利。老板看他哭的莫名奇妙,尴尬极了,“小伙子,大清早你在我这哭,我怎么做生意?”苏朝晖边哭边说,“你别管我,好吃我才哭,我这是帮你揽生意!”老板嘿笑,“思路还挺清晰,失恋了吧?我也受过爱情的苦,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和尚动凡心。”苏朝晖说,“我考试没考好,我不想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