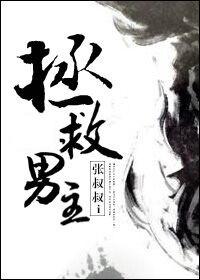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百年江山三部曲 > 第103页(第1页)
第103页(第1页)
在余丹波的话后,祠堂里有一阵的寂静,袅袅香烟旋绕在他们的上头,案上日夜不熄的白烛,闪闪摇曳。“将军,王爷亦是身不由己啊。”两手叉着腰的燕子楼,边说边摇首叹息,“要去向阎翟光低头的人不是将军,而是王爷,他心里的苦,你又怎会明白?”一阵鼻酸,伴随着泛上心头的不舍,顿时一涌而上,根本就不愿意去想象玄玉将如何说服自己踏入阎相府的乐浪,心里的矛盾,拉扯得他好疼。余丹波撇过脸刻意不看他,“你要真为王爷心疼、为王爷着想,你就该将你能为王爷做的事做好。”知道他在示意些什么的乐浪,过了很久后,努力将话挤出口。余丹波嘲弄地瞥他一眼,“你以为我和你一样不长进吗?”“余将军……”燕子楼已经很想拜托他留点口德了。在燕子楼与乐浪没好气的目光下,余丹波不情不愿地开口。“我都已盘算好了,现下,就等你们来帮我。”日夜兼程赶回长安,进宫面圣上禀九江现况后,出宫的玄玉方登上乘舆,随即朝外头的堂旭交待设法甩掉太子派来跟在他后头监视他的人。了解玄玉不想被太子察觉行踪的堂旭,随后向手下作出的安排,在出了皇宫即派来另一座简朴的小车让玄玉换乘,而原来的官舆则是照原定计划返回齐王府。“到阎相府。”在堂旭坐至车头驾车之时,车里的玄玉低声吩咐。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内,心思百般复杂的玄玉,眼前不时闪过素节当年的笑脸,与在九江时乐浪忿怒的面孔,他用力合上眼,企图甩脱开来,一再地在心底复习着袁天印曾对他说过的话,他努力告诫自己,纵使再不愿,他也得向现实低头。因此在朝中一收到阎相私底下派人传给他的字条之后,手握字条的他,虽不知由余丹波找来的尹汗青究竟是如何打动阎翟光,让阎翟光主动找上他的,但他知道,尹汗青想必是费了一番工夫,为了他身后在日后还得仰赖他的众人,他不能不来。颠簸的马车停止了行进,刻意选在相府后头小门停车的堂旭,详细观察了四处的情况后,趁着没人瞧见,赶紧将玄玉迎下马车,随着已在小门处等候他们许久的总管入府。在得知玄玉回长安后,急欲见他一面的阎翟光,在厅堂里斥退左右,就连堂旭也一并给请出堂外后,坐在椅内默不做声地看了玄玉良久。“你得了个能手。”打破沉默的头一句话,指的是谁,他俩都心中有数。坐在他对面的玄玉,谦虚地颔首,“相爷过奖。”阎翟光却缓缓摇头,“尹汗青虽能言善道,但你这上头的主子是否真如他所说一般,可就未必。”“本王可曾令相爷失望?”玄玉笑看着这个在灭南之战前,向圣上主张任他为大元帅的老人。“但你这回的对手可是太子。”沙场与官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子事,沙场上他或许得意,但官场侥幸胜出,则还是个未知数。“还有凤翔。”玄玉提醒他忘了尚有一人,“我听底下的人说,凤翔已展开行动,正朝外戚这一势力靠拢。在我与太子交锋之前,凤翔的所作所为,将会令太子先行找上他开刀。”在朝中四处有眼线,消息灵通的阎翟光,当然知道凤翔在远赴巴陵之前,在私底下已晋见过皇后,至于那名突然冒出来,在朝中与国舅走得很近的文翰林,他也知其效力于何人。他把玩着手中的扳指问:“以你看,凤翔胜面如何?”“太子位居东宫乃杨国储君,即便母后有微词,若无动摇国本大事,父皇不会动太子分毫,再加上太子门人在朝中助威,因此凤翔在短期内就算有母后在旁使力,太子胜面仍是较大。”将自己分析之见说出之后,玄玉语带保留地顿住了话尾,“只是……”“只是?”他别有用心地看向阎翟光,“只是凤翔若掌握住太子把柄,再加上他人之势欲拖太子落马,两派之势齐攻,双拳难敌四手,即便太子再如何占尽风流,太子之位也恐将堪虑。”一点就通的阎翟光,饶有兴味地挑高了两眉。“老夫若没听错,方才你可是在说,你愿与凤翔联手扳倒太子?”玄玉不急着否认,“联手倒未必,眼下,本王只打算冷眼旁观。”他不过想坐收渔翁之利罢了。阎翟光刻意深叹了口气。“再怎么说,太子总是你的亲兄弟。”从方才到现在,在他的话里,皆无一丝手足之情,再三确定他是否真能绝情的阎翟光,必须先把这点弄清楚,免得在日后才来后悔选错人并因此处处制肘。“太子可会放本王一马?”玄玉的面色逐渐变冷,“御使是如何死在丹阳的,相信相爷心底应当有数。”太子想杀他,连局外人的玉权都清楚,站在太子近处的阎翟光,岂会有不知的道理?阎翟光喃喃笑问:“你这是在怪老夫没阻止太子?”“怎会呢?”玄玉四两拨千斤地带过,“太子对本王怀有成心,本王早就知情,这事怪不到别人身上。”“有件事,老夫想问你。”对他仍是有些担心的阎翟光,再次挑出了个攸关他性命的话题。“相爷请说。”“你是否仍与乐浪走得近?”乐浪恨他入骨,全朝皆知,身为素节皇弟的玄玉,没理由不恨他,要是日后玄玉在事成之后来个秋后算帐,他岂非送羊入虎口?玄玉朗声笑道:“相爷何不直言本王是否仍对皇姐之事耿耿于怀?”“是,或否?”目光专注的阎翟光,固执地想得到答案。“真要挂意此事,本王不需找上相爷,真要对相爷保持成见,那未免也显得本王目光浅短。本王是要成大事之人,而非沉湎于昨日之中的愚者。”早在心底编排好一套说词的玄玉,说来没有一丝迟疑,“相爷若担心本王在日后将会翻脸清旧帐,那么相爷就太看轻本王了,无论过往前尘再如何,本王还不至会对自己人下手。”“看不出来你倒是挺看得开。”安下心的阎翟光,脸上的神情明显地似松了一口气。他耸耸肩,“时势所逼。”“对了,在你手下,可有袁天印这人?”颇讶异他会突然提及袁天印的玄玉,只怔愣了一会,立即聪明地选择不在他面前装傻。“有。”他又再问:“你可知袁天印是何人?”“知道。”看样子,阎翟光不只是详知朝中动态,就连袁天印的底细,他可能也已经摸透了。“你可知袁天印与我是同乡?”可说是全杨国惟一知道袁天印出处的阎翟光,徐徐道出袁天印的来历。“本王从不过问师傅之事。”玄玉状似不以为意,“师傅若愿说,师傅自会告知。”“你信他?”玄玉反问:“不信,何以统管洛阳?不信,又何以灭南?”阎翟光不得不提醒他,“为达目的,袁天印同老夫一般,皆不择手段。”“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玉权死后,他就已得到了这个结论,“今日师傅既有心助我,本王自取信于他,同理,今日相爷若愿提携,本王自当也对相爷深信不疑。”“你可知袁天印为何弃玄玉而去?”怕他生毁的阎翟光,不死心地再抖出袁天印与他极力想隐瞒的事实。“既然相爷深知师傅的性子,那么相爷就更该相信本王,本王绝不会让师傅失望。”往后靠坐在椅内的玄玉,以自信的眼神看向他,“同样的,本王亦不会让相爷失望。”原本犹在摇摆的那颗心,在玄玉的保证出口后,终于止定了下来,明知这是场风险极大的赌注,不得不为日后盘算的阎翟光,端来一章小桌上的茶碗,起身走至玄玉的身旁落坐。“你可知太子即将收回三地?有何因应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