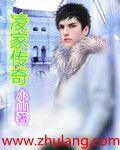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病弱前夫是朵黑心莲晋江 > 第145章(第1页)
第145章(第1页)
仿佛要将这些日子里的难过与委屈都哭出来一般。
她的哭声由低转高,再转为细细的啜泣,良久方勉强收住,只剩下压抑的一点泣音。
当她慢慢抬起头来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件月白色的常服。
沈陶陶微微一愣,哽咽着慢慢抬起眼来。
她的眼里蒙了一层薄薄的泪光,看一切的事物都仿佛浸在水中,眼前之人的面庞也看得不甚真切。
只依稀得见,那熟悉的,素日里肤色冷白,神情冷淡的面上,已蒙上了遮掩不住的憔悴之色,眼底略有青黑,下颌上也已攀上了淡青色的胡茬。看着倒不像是辅国公府里的世子,反倒像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落魄公子。
此刻,他正轻抬着手,掌心握着一方干净的方帕,似乎是迟疑着不知该替她拭泪,还是该放在她眼前的窗楣上。
明明是这样熟悉的脸,不知为何却是这样陌生的狼狈模样,与她从未见过的惶然无措。
宋珽也正垂目看着她,鸦羽般的长睫与胸腔中那颗剧烈跳动的心脏一同颤抖。
他本立在庭院中,但遥遥地,听见沈陶陶的哭声,便觉得心中一阵发紧,明知不该,却还是一步步地绕过了围墙,行至她的窗前。
彼时她正趴伏在窗楣上,哀哀痛哭。
她一头青丝未束,凌乱地贴服在脊背上,而身上穿得还是一件月白色的里衣,赤足上也未着鞋袜,显得分外的伶仃可怜。
他与沈陶陶两世相识,却从未见她哭得如此伤心。
这不得相见的日日夜夜中,那翻滚在喉间的话语,在此刻,在沈陶陶的哭声中,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口了。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她,也从来没有人教过,这个时候该怎么做。
宋珽沉默了良久,终于将帕子轻轻放在她眼前的窗楣上,哑声道:“上一世的事,若你恨我,我可为你抵命。”
他以为如此,沈陶陶便能高兴起来,孰料,沈陶陶闻言哭得更凶了,还‘砰’地一声将长窗关了,彻底隔绝了他的视线。
宋珽无措地立于原地,似乎想伸手叩一叩窗楣,但又怕惹得沈陶陶愈发不快。
僵持了一阵,他倏然看见,江菱带着顾景易疾步走来。
宋珽慢慢地收回了手,转过身定定地看着两人。
他看着江菱为顾景易开了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