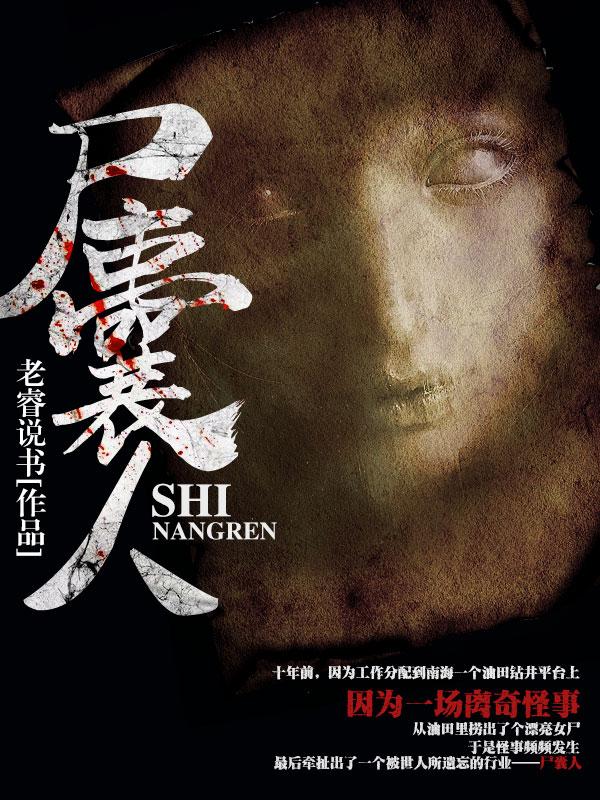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万万没想到准太子是我全文阅读 > 第214章(第1页)
第214章(第1页)
“且慢。”华阳郡公忽然叫住杨景澄,“你弄的比武大赛每年花销不少?”
“放心,”杨景澄咧嘴笑道,“有钱撒钱那叫有本事,没钱打肿脸充胖子那叫二傻子!我订赏格之前算过账的。再说了,我们家为什么有钱?还不是几代人都不爱出去厮混,从没哪位爷包小戏子捧角儿的么?那才是金山银海。我一年花二千两在衙门里,很节省了好不好!她再想克扣,那也是得要脸的!”
华阳郡公笑出声,没再多说什么,挥手示意杨景澄可以滚了。杨景澄也不客套,径直走回正院,接了颜舜华便走。夫妻两个在马车上并没有说话,而是回到了家中,照例把众人撵了出去,方开始交谈——这也是夫妻议事的好处,与旁人说悄悄话儿总容易被人猜忌,但两口子爱凑在一处说话,旁人最多只往那上头猜,很少会觉得他们在商议正经事。
杨景澄率先开口:“嫂嫂同你说了什么没?”
颜舜华摇头:“大抵就是前日的话,无非在家里说的更细了些。郡公如何说来?”
杨景澄苦笑了一声:“他让我对长乐客气些。”
颜舜华愣了好半晌,才试探着问道:“大家演戏?”
“不是。”杨景澄脸色有些阴沉的道,“你想想,如果没有长乐,宗室里只有华阳哥哥一枝独秀,会怎样?”
颜舜华第一反应是好事,然而很快她就脸色一变!孱弱的君王,强势而受拥戴的太子,让她没来由的想起了史上西晋太子司马遹。一样是擅权的内宫,一样是懦弱的皇帝,一样是……幼而聪慧名望过人的太子!
满朝文武都没有拦住贾南风的毒手,到头来落了个“不修德业,性刚且奢侈残暴”的评语,这怎么可能是年仅五岁时说出“暮色仓猝,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之语的太子该得的评语?而诸如在宫中“切肉卖酒,以收其利”荒诞,岂知不是在自污?然便是自污到史上骂名,不也没逃过任人宰割的宿命么?
杨景澄见颜舜华脸色发白,知道她大概是听懂了,过了好一阵,他有些艰难的道:“长乐郡公夫人……亦是我们表姐。她同你示好,你……就多与她亲近吧。”他自己不愿向长乐低头,却要颜舜华去与人交际,实在有些无耻了。
颜舜华不以为意,柔声道:“你与长乐之事,我听外祖说过。既是闹翻了,你再去同他说话倒叫人看轻。而我这边则不同,她先来寻的我,所谓‘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我同她来往是我知礼不张狂。既从了郡公的话,又对我的名声大有好处,何乐而不为?”
杨景澄握住颜舜华的手,郑重的道:“多谢。”
颜舜华咯咯笑道:“龙景澄你不行啊!不是说当官就得心黑手狠脸皮厚么?你脸皮怎么回事?小时候挺厚的,越长越回去了?”
严肃的气氛陡然一松,杨景澄想起华阳郡公那句“我们还年轻”,渐渐放松了下来。所谓宦海沉浮、步步惊心,艰难险阻总是无穷无尽,为了这点子事便一惊一乍的,确实太沉不住气了。于是伸手往颜舜华脑袋上推了一下,笑道:“我那是怕你受委屈!好心没好报!”
“嗤,”颜舜华鄙视的道,“京里的男人一个比一个有病,养出来的闺秀自然一个比一个没用。凭她们也想欺负我?”
杨景澄鼓掌:“女侠好风采!”
“滚你的!”颜舜华正色道,“不与你说笑,外头的事我真不知道几件。你与长乐郡公的而纠葛,还是我临出门前外祖急急告诉我的,为的是我对上他夫人不吃亏。”说着十分不满的撇嘴道,“我寻思着后院起火不是个好词儿啊,这些当官的男人一个两个的生怕女眷知道了一丁点儿外头的事,怎么着?盼着后院起冲天大火吗?”
杨景澄喷笑出声!还真是,朝堂官员栽在女人身上的可不少,张继臣不就是被小妾和丫头坑了的么?
“你别笑,听我说完。”颜舜华道,“所以你把同你好的,同你不好的,都列个表给我。另外,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你正经弄点书回来给我。你那书房……我就不耻笑你了。”
杨景澄确实不太爱读书,讪笑了两声道:“谢谢你没提我的字哈。”
颜舜华扶额道:“你的字儿是该练练了,跟我写的差不多叫怎么回事儿?”
“你可真谦虚!”杨景澄半点不在意老婆比他强,现朝堂还是章太后当家,见女人强就不自在,直接趁早上吊得了。何况字这种东西,无非是多想多练,颜舜华有空练的多些、写的好些不足为奇。
遂笑道,“买书的事好说,你开个单子给龙葵,以我的名义买便是。”末了,又嘱咐道,“你让他送到内书房来,你看书的时候别露了痕迹。叫人看见你正儿八经的读《四书五经》,又是一堆闲话。”
颜舜华很不高兴的道:“圣人还说有教无类呢,到他们嘴里就成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了。”
杨景澄无奈的道:“谁让圣人死了呢?他死了自然是别人说什么便是什么了,他又不能从坟里爬出来打人。时下风俗如此,我倒不怕人笑话,只怕你有个才女的名头传出去,反倒不好与那些妇人交际。
你要明白,越没本事的人心眼儿越小。妇道人家镇日里被关的死死的,从未见过外头的模样,还一个个的认不得几个字,哪里来的心胸开阔?你本就生的不赖,再添个才貌双全,只怕寸步难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