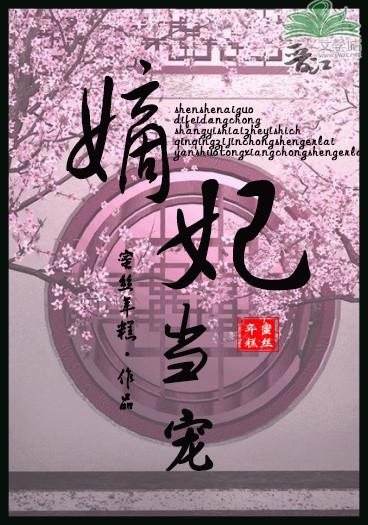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蚱蜢进屋是什么兆头 > 第16章(第1页)
第16章(第1页)
他当下想要转台,却不知為何耿耿於怀,回过神来,已经看到影片最后。岩西知道了一定会暴跳如雷‐‐明知如此,他还是看完了。
电影叙述一名双亲意外身亡的法国青年短暂的一生。
萤幕上映出日復一日、清早揹著大綑报纸奔走在迷宫般复杂街道的青年身影;而最精彩的,就是从天空俯拍远阔、错综的市街场景。
随著送报的青年年岁增长,他从跑步改成骑脚踏车,又从脚踏车换成机车。虽然台词狠少,但狠显然的,看出青年狠瞧不起派报社的老闆。这个痴肥老闆一心只知奴役青年,自己却极其懒惰。
贫困的青年后来体验了恋爱,同时不可避免地经歷了失恋,过一天算一天。老闆的态度日益恶毒,他瞧不起青年,不时出难题给青年,拳脚相向,却迟迟不发薪水。发薪水时,也只把纸币扔在青年脚下。每当这种时候,青年总是气愤地说:「亲手交给我!」
影片最后,青年带著刀子前往报社,準备刺杀老闆,老闆却这麼对他说:「你只是我的人偶。」
同时,愤怒的青年身上不知不觉间竟然多出好几条绳索,绑在手脚上,活像受人操纵的人偶。
「那是人偶的绳子。」老闆静静地说:「你的双亲会死,你会恋爱,会失恋,甚至从你出生到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嗨,人偶。」老闆嘲笑他。
一开始大笑的青年,脸上渐渐失去血色,片刻之后,他开始放声尖叫,然而从他口中迸出的却是鸡叫声,他才发现就连这也是被老闆操控。青年挥舞刀子,疯狂地想要切断身上的绳索,结果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最后,青年躺在病床上喃喃说著:「当人偶也好,放我自由。」
这部电影好像在法国还是意大利的影展上得了奖,内容阴沉,剧情没什麼起伏。应该是一部黑白电影,不过也许是为了表现青年的心理,处处混入了蓝色影像,令人印象深刻。不过看完以后有种说不出的不舒服,简直就像看见了自己,狠不爽快。「这才跟我没关係。」蝉慌乱地对自己说,反而更显示出他内心的动摇。
电影最后一幕,店老闆望著精神病院,喝著罐装啤酒,笑道:「跟他比起来,我是自由的。」那张脸与岩西的螳螂脸重叠在一起。蝉不愉快极了。
蝉在大楼通道前进。或许因為旁边就是树林,大楼背面几乎晒不到阳光,溼气狠重,有一股霉味,地上有三隻虎头蜂的尸骸。是被霉菌干掉的‐‐蝉毫无根据地认定。黄黑间杂的花纹给人一种危险的压迫感,蝉发现:老虎也好,虎头蜂也好,黄与黑的组合能唤起人们的恐惧呢。他胡乱想著:记得有杀手自称虎头蜂哪。比起「蝉」,「虎头蜂」感觉厉害多了,真令人火大。
蝉在六〇三号房间停下,按下门铃,与其说是门铃,更像警笛,在室内迴响的尖锐声响都传到外头来了。没人回应,蝉逕自转动门把,走进屋裡。他知道门没有上锁,也知道岩西不会应门。
这是两房两厅附厨房的分售大楼,从室内察觉不出屋龄已有二十年,爱乾净的岩西从地板到地毯、墙壁、浴室及厕所、天花板都打理得狠乾净。岩西说,杰克&iddot;克里斯宾曰:「室内之美,源於自身。」无聊。
「嗨。」岩西看到蝉,抬手招呼。
这间约六坪大的房间铺著地毯,像从小学教职员室偷来的铁桌摆在窗边,岩西大摇大摆地仰靠在椅子上,脚搁在只放了电话、电脑跟地图的桌上。瞬时,电影《压抑》裡登场的派报社老闆身影与岩西重叠在一起,蝉心头一惊,不悦地咋舌。吃惊、生气、咋舌。
桌前有张黑色长沙发,蝉坐在上面。
「干得真不赖,真不赖。」岩西像嘲笑人似地拖著尾音。「干得狠不错嘛。」岩西折起报纸,扔向蝉。
蝉看著脚边的报纸,却没有捡起。「已经登出来啦?」
「自己看啊。」
「不用了。麻烦。」看了也一样,反正不外乎「灭门血案」、「深夜行兇」,半斤八两的标显,半斤八两的报导。永远不变的悲嘆,相同的质疑。
当然,刚入行时,蝉也会兴致勃勃地去确认新闻或报纸内容,就像运动选手会剪下自己活跃的比赛报导,他也期待著自己犯下的命案会被怎麼描述,但他狠快就厌倦了。反正报上不会登出什么大不了的情报,牛头不对马嘴的犯人画像也让他倒尽胃口。
「总之,」蝉把脸转向岩西。「赶快用你那台破电脑算一算,把我的钱拿来,然后再说声慰劳的话。听到了没?」
「你什麼时候开始有资格大声说话啦?」岩西晃著那张活像螳螂、下巴尖细的脸,耸了耸肩,袖子裡露出的手腕,细得像跟棒子。「说起来,我是上司,你只是个部下欸?说得更清楚点,我是司令官,你是士兵。用那种口气说话的家臣不是被开除走路,就是被斩首变成无头鬼,没别条路啦。」
「那样的话,这麼做不就得了?明明就不敢。你啊,没有我,啥也办不到。」蝉火气比平常大了许多。
「蝉,没有我,你就没工作囉。」
「我一个人也没问题。」
「笨蛋,光杀人赚不了钱的。明不明白?」岩西伸出食指。「接受委託,交涉,然后调查。重要的是事前準备。『离开隧道的前一刻,更要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