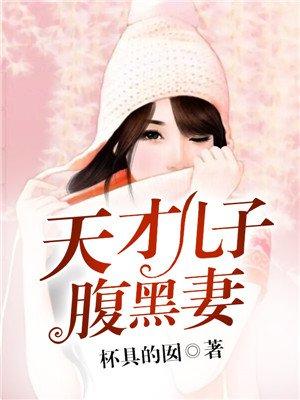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贵妃总想弄死朕无弹窗 > 第199章(第1页)
第199章(第1页)
性子转了,气色也比从前好了许多。
从前不管喂她多少金齑玉鲙,她都长不了几两肉,甚至在怀阿留的时候还瘦得让人看着心惊。
如今虽然还是痩,但没有从前那种易折脆弱的感觉了,皮肤白皙莹润,由内而外透出来一股熠熠神采,仿佛整个人披了层珍珠的光泽,柔和温婉,安谧娴静,看着就让萧逸觉得很安心。
怀中传来轻浅且均匀的喘息,楚璇这觉果然来得快,没有一炷香就窝在萧逸怀里“呼哈呼哈”地睡着了。
萧逸搂着她在绣枕歪了一会儿,便将她轻轻放回床上,起身出去。
外面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去处理。
如江淮所言:人死债消。对于萧佶,他应当彻底放下十几年的执念与仇怨,开始过新生活了。他也该相信江淮对他说的,徐慕在天有灵,看着他这么多年为了给义兄报仇而付出的一切,看着今天这样大好的局面,也该安息并痛痛快快地去投胎了。
恩怨已了,活着的人得好好活,连江淮那愣小子都懂的道理,没理由他要一直纠结。
因而回了宣室殿,便命人召楚晏,他该传的话传了,后面的事该怎么处理就由他们去吧,左右不过一具尸体,总不可能送回胥朝他就能活过来吧……
楚晏接下话,又问了问楚璇的近况,才依旨告退。
龙案堆积了些奏折,萧逸估量着楚璇这一觉还得睡些时候,便沉下心来批了一些,待日落树梢,天光暗沉,才赶着晚膳的点回昭阳殿。
还没进殿门,远远就看见他母后身边的翠蕴和楚璇身边的霜月、画月都守在殿门外,宫人们齐刷刷地跪了一地,向萧逸鞠礼,他站定了,一脸严肃、居高临下地低头问霜月,“里面是什么情况?”
霜月微低臻首,颇为含蓄道:“这情况就是……陛下还是躲着点吧。”
这丫头俏悦的话音甫落,殿里便传出太后的声音:“思弈,你来了是吧?进来!快进来!”
萧逸愣了愣,瞬间面如死灰,抬手捂住前额,硬着头皮、表情僵僵地进去了。
“你来评评理。这是云州进贡的绉罗纱,轻薄丝滑,正是当季穿的。哀家想着让尚衣局制成衣衫,赶在入秋之前还能穿个鲜亮。可衣衫好制,首饰难配,我想着璇儿那里正好有一套银钗攒猫儿眼的头面,就想借过来用一用。是借,不是要,等尚工局把首饰打出来哀家就还给她,你说她怎么这么难说话,就这也不答应,亏得只是一套银饰,还没值多少钱……”
萧逸转头看向楚璇,见楚璇鼓着腮,咬着唇,一脸忿忿不平,就是不说话。
萧逸瞬间头大,为了表示公允,还是在她充满怨念的眼神里,温声道:“你说话,母后都说了,你也得说,不然朕怎么给你们断官司?”
楚璇双眸水润莹莹,可怜兮兮地道:“三月的时候,太后说她新制了襦衫,把我的赤金嵌红宝凤钗要走了。四月的时候,她说天气沉闷,得配清亮些的首饰,又把我的珍珠梅花冠要走了。六月的时候,她说天气渐热,容易烦躁,得戴轻一些的首饰,把我的十二支翡翠点绛珠细钗要走了。刚进八月的时候,她说我怀孕了,戴不着多少东西,放着也是浪费,命人开了我的螺钿匣子,划拉走了一大半……”
她低了声音,嗫嚅:“这哪是首饰的事,分明是在欺负人……”
楚璇一觉得委屈,那张雪腻剔透的小脸就皱在了一起,秀眉拧着,几乎要打成结,看得萧逸心疼不止,刚想伸手抚平她的面颊,恍得接收到他母后要杀人似的锐利眼神,讪讪地又把手收回来,挪了挪身子,坐在她们两中间,谁也不偏靠。
这女人的事,就跟圃篓里的丝线,绞缠在一起,乱成个结,难以拆解,纵然英明神武如皇帝陛下,也还是难觅良方。
他没办法,可这两女人却不打算放过他,各自陈述完毕,目光炯炯地看向萧逸,等着他给个评判。
萧逸伸出一根手指,挠了挠自己的额角,轻咳一声,道:“那个……不就是点首饰的事嘛,库房有得是,等用完了晚膳朕带你们去挑,想要什么样的拿什么样的,想要多少拿多少,拿回来呢就戴自己的,别去抢别人的。”
这话听上去很合情合理,谁料太后眼一瞪,怒道:“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也嫌哀家抢这小妖精的首饰了?哀家是太后!把你从小丁点养到这么大,你如今娶了媳妇就不要娘了是不是?你个小没良心的!”
她身体强壮,说话中气十足,跟破风凌空射来的利箭一般,‘飕飕’的戳到萧逸的脑门上,把他戳得头‘嗡嗡’的疼。
萧逸捂着头,随波逐流地道:“对……您是母后,您把朕养大很不容易,朕不应当因为这点小事忤逆您……”
“话也不是这样说的。”楚璇不乐意了,一脸严正地开始讲道理:“是,太后把陛下养大不容易,您又是母后,做儿媳的孝敬您是应当的,可凡事得有个度吧。您不能仗着是陛下的母后一个劲儿在这儿欺负人啊。我都忍您许久了,想着您是个通情达理的,能知道我的一片心,该体谅我,该疼疼我了,谁知道您非但不知道心疼我,还变本加厉,这样的日子谁受得了啊。”
“你怎么就受不了了?不就是拿你点首饰,你那些东西都是我儿子给的,哀家拿了又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