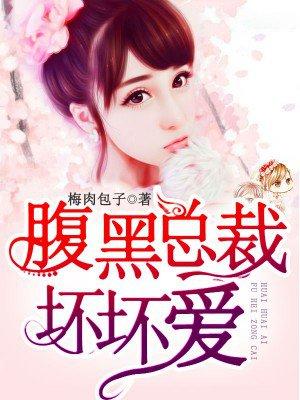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囚·锁by清秋凉意 > 第89章 行道迟迟(第2页)
第89章 行道迟迟(第2页)
“若是不吃,今夜不用睡了。”
说完,他无视谢栀投来的眼神,走到浴房,就着她用过的水匆匆沐浴。
出来之后,见人又重新睡下,碗里的银丝面已然空了。
裴渡心下稍定,脱靴上榻,躺在外侧,闭目良久,少顷开口道:
“给你一次机会,不能再做出下药那般龌蹉之事,也不能再一声不吭地跑走,这不是好孩子干的事。”
床内人不回话,但裴渡知道她没有睡着。
“你不知道,你上回藏身的稻田,后面就是一座山林,那山林里常有大虫作怪,上月刚咬死过人。”
“还有,就算你安全出了城,可知南边路途有多远?那头最近出没不少流寇,杀人不眨眼,极其残忍。似你这般相貌的年轻女子,独自出行,犹如小儿抱金过闹市,想不被人注意都难。”
裴渡说着,目光转向床内,盯着她的背影道:
“要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老老实实跟在我身边,有什么不好?”
谢栀心绪烦躁,不想听他老僧念经,将被子掩过头顶,默不作声地装睡。
只是又如何能睡得着呢?
默了片刻,她在一片黑暗中出声:
“大人,我的那些画呢?走之前我让院里的绡翎,送给昭音做新婚贺礼的,可回来之后,昭音没有收到。”
“烧了。”
“什么?”
谢栀惊坐起身,推搡着一旁的男人:
“裴渡,你没骗我吧?”
裴渡冷哼一声:
“我方才说了那么多,你都爱搭不理,一说到你画的那些东西,倒来精神了?”
见他一幅毫不在乎的态度,谢栀更加急切:
“那些是我画了半个月的小人书,一早装好了,还细细用最好的松烟墨描了色,裴渡,你是不是骗我的!”
“你画的那些东西,设色虽大胆,可雅致不足,十成十的艳俗,如何上得了台面?往后也不要再画了,有这功夫,好好在府里学些规矩,没得整日做些惊世骇俗之事出来,叫人头疼!”
裴渡说完,拍了拍一旁的榻道:
“快睡,别折腾了!”
谢栀的手死死绞着被衾,气得脑袋胀疼:
“裴渡,你真是古板得无可救药!”
裴渡听到这话,一边下床熄灯,一边冷笑:
“没规矩,等到了都护府,我必给你请个女先生,教教你何为柔顺之道!”
他说完,又重新躺下,似是赶了一日的路有些疲惫,很快便沉沉睡下了。
谢栀却是彻夜未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