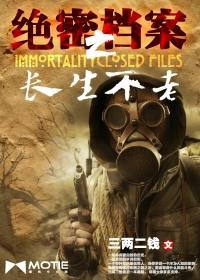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锄禾日当午的诗人 > 25弹棉花(第2页)
25弹棉花(第2页)
弹好了棉被姑娘要出嫁
唱者无心,听着却是有意,锄头听着田小午这曲子里的“弹好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不知为何,浑身像是登时充满了干劲,弹得更欢实了。
锄头力气大,耗费了一下午的气力,那床本是年头久远的又硬又黑的棉絮,一经这番重新弹制,便又洁白柔软如新,很是神奇,田小午帮着锄头压磨一番,使之平贴,便又是一床新棉絮了。
吃罢了晚饭,锄头干了大半天的活,又弹了那一下午的棉花,很是劳累,便早早的睡去了,田小午却在油灯底下兴致勃勃的做她的被子。
下午锄头在院子里弹棉花的时候,田小午已是将那干了的被面里子铺开来,翻过来反面朝外的缝好了三面,又用上次做裙子留的碎布头将那些烂着的破洞给补好了,一回生二回熟,做过了一回衣裙,田小午这次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干起来很是轻车熟路,棉布虽大,但不过是四个边角,手工花样做起来却是最简单的,田小午做的得心应手。
如今又将那缝好的被子表里平铺在凉席上,将那弹好的散乱蓬松的棉絮一层层的铺上,层层叠叠的絮匀了,等这棉絮将一床被子都絮满了,便用针线松松的牵引缝制几圈,将这棉絮跟下面的棉被的里子粗略的勾缝在一起,再由那开着口得一头慢慢的将这棉被给翻过来,这般一来,棉絮便被翻进了里面,被子的雏形已是出来了,将絮好的棉被用针把最后留着的那一溜被边缝好,这棉被便就做好了。
为了防止自己絮棉花功力不够,这棉絮在被子里乱跑,田小午又将被子翻过来被子里子朝上,飞针走线的又缝了几圈才作罢。
田小午看着自己做好的棉被,因那略显粗糙的针脚隐在被子里面大看不出来,这般粗略的看去,软和厚实,蓬松干净,还带着股阳光的味道,很是满意!
在上面舒舒服服的打了个滚,心里成就感极度的泛滥,要不是那伤腿不便,她怕是要翻个跟头以抒发自己内心的得意自豪呢!
成功总是鼓舞人的,首战告捷的田小午第二日一鼓作气势如虎又将那床铺着的褥子也依法拆洗翻新了一遍,当然,锄头还是客串了那弹棉花的重要角色,不过,田小午只知道被褥是她做的,锄头那不可磨灭的功劳已被她给暂时忽略不计了!
这秋庄稼刚刚种上,布谷鸟的呼唤从窗外声声传来,喜鹊也在枝头蹦的长的欢喜,这几日田里已是不太忙,旺子村的庄稼人一大早除了男子照例下地拾掇田地之外,女人们却是闲暇了下来。
锄头照例早早便上了山,田小午在院子里浇她那已经打花苞的一溜扁豆南瓜,远远的就听到一声接着一声的的叫卖声,“赊小鸡了呦,赊小鸡不?”,“赊~小鸡儿嘞——好~小鸡儿!”
……,悠扬嘹亮,绵软悠长,荡漾在这个绿荫四合的小村庄上。
在这农村没几户有钱的人家,这买小鸡大多是按照惯例赊鸡。
春天赊鸡,按照赊购的数额,都记在卖鸡人的账簿上,农村人有识字的人自己写,不识字的人由邻居代写,有些信得过的也央卖鸡人来写,待到秋收后卖鸡人来要鸡账。那时的小鸡已经长大,又是庄稼丰收的季节,淳朴厚道的乡里人自会一份不落的把所欠的钱还上。
按理说这麦子收了,已是过了那春夏之交的小鸡出炕的时节,多少有些晚了,不该还有赊小鸡的来的,田小午疑惑的透过篱笆门向外看去,看清楚了的确是农村走街串巷的卖鸡人。
只见那赊鸡的汉子头戴苇笠,脸热得通红,肩上用桑木的上弯扁担挑着底部是四个撑的方型木托,上面是用树条儿编成的大圆箩,忽闪忽闪地,边走边吆喝,一路从邻村方向走来往城镇上去,正路过锄头家门口。
田小午当下正想养鸡呢,便叫住了那赊小鸡的汉子放下担子,锄头家虽是村头,但却是进城下田的毕竟之路,人来人往的行人三三两两络绎不绝,这番见到赊小鸡的,好多人都停了下来,有些热心的女人则赶着回村去吆喝街坊四邻。不多久,这东邻西舍的大娘小媳妇,纷纷出门,围拢了来,小孩子们也欢呼雀跃着,拿着小提篮或簸箕,跟随母亲婶娘,兴高采烈的涌来看大人们挑选小鸡。
等田小午从锄头院落里跛着脚出来,旺子村没下地的大人小孩都已是闻声出门,早已是人头攒动的围在装满小鸡的竹筐旁边。
作者有话要说:某遥只见过弹棉花,但没亲自弹过,但却是老老实实的去百度上找了资料,
用木捶也是可以弹棉花的,
那首《弹棉花》很是欢快,有农村小调的味道,
某遥剽窃来了……
啦啦啦
下一章,锄头家有新住户了……
O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