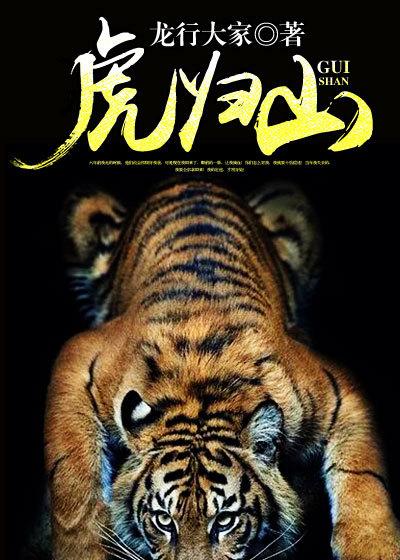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弃妇娘亲太嚣张全文免费 > 第11章(第1页)
第11章(第1页)
”周涛瞧他不起地翻翻白眼,往嘴里扔了粒花生米,嘎嘣嚼了,“你小子不够意思啊!人家丁大夫为你都做到那种地步了,你还装得跟什么都不知道似的,不是爷们啊!”这话着实冤枉晏秋了,他听到“丁大夫”三个字,顿时吃了一惊:“丁大夫?关丁大夫什么事?”
周涛真郁闷了:“我说,不带你这样儿的。做人要实在。”然而瞧着晏秋的脸,不由张大嘴巴:“你不会真不知道吧?”
晏秋诚实而茫然地摇摇头。
周涛真正没话说了:“你这人真是,我该说你不关心自家生意呢,还是说你什么好呢?金家布坊开张那一日,请了不少人贺喜。那一日丁大夫领了她家小丫头,挤开多得堵到你家门口的宾客,走进秋水阁,一人抱了一匹浅色的绢纱出来。那金家布坊走的是丝绸,她就到你家买纱布,可不惹恼了人?”
“然后呢?”晏秋捏着杯子。
“吵起来了呗。要说丁大夫跟她家那叫什么归的丫头,都是好样儿的,一个敢作敢当,一个口尖牙利,那样一堆人,愣是没讨了好去。”周涛偷闲喝了杯酒,咂摸着嘴。
晏秋愣愣听着,心里边不知道什么滋味儿。
“你小子,艳福不浅。”周涛笑骂道,“可怜人家丁大夫,那样鼎力相助你家秋水阁,可是你这做掌柜的,竟然不知道人家。”
晏秋无话可说,自罚一杯:“我今日上午刚刚回城,还没听说此事。多谢大哥告知我,回头我便命人拎了谢礼,谢过丁大夫。”
“不解风情!不解风情!”周涛直道他装,可是转念一想,这事换了他大约也是一样。于是瞅了瞅晏秋,问:“我说兄弟,你今年二十有四了吧?也不见你着紧婚事。平日里连花酒都不见喝,你真就是和尚咋的?也不知你心里咋想的。哥哥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是两个娃子的爹了。”
晏秋抿唇笑:“我一个瘸子,又满身铜臭,哪家姑娘能看得上我?”他因为几年前受过伤,左脚有点跛,虽然平常看不出来,但是走快了还是十分明显。
周涛却不爱听,手中酒杯重重磕在桌子上:“什么叫瘸子?你脚上那点毛病若不仔细看,鬼才瞧得出来!怎么又说满身铜臭?钱财是坏东西吗?再者说,你晏秋晏大少的名声不够响?排在你家门前给你送手绢的姑娘嫌少还是怎的?”
“哎哟,跟你说话我就来气!”周涛捂着胸口,恨铁不成钢地瞪着他。
晏秋则哈哈大笑:“排在我家门前送手帕的姑娘?我一个也没瞧
见。大哥瞧见了?觉得如何?哈哈,不如带回家给嫂子瞧瞧,看看哪个更俊俏些?”
带回家?他不要命了。周涛恼羞成怒,伸出胳膊在晏秋肩上狠狠擂一拳,解了气,也笑了:“要说你嫂子,那是陪了我不少年头。吃了那么多苦,从无怨言。我周涛这辈子有她,不说美人,就是金山银山,再大的官儿,我也不能负她。”
要说他家婆娘,哪里都好,就有一点,就因为没给他生个儿子,就老偷偷躲起来抹眼泪,还要给他纳妾。
可他能吗?他又不是忘恩负义的畜生,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
晏秋拿起杯子,遮住眼。碰着秀恩爱的了。要换了别人,他早打他一顿出气。可是碰上周涛,只得默笑。
周涛又道:“啥时候兄弟也碰见一个愿意为你舍身枉命的女人,不论她相貌如何,心地如何,娶了便赚。”
“那倒是。”舍身枉命?哪有那样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