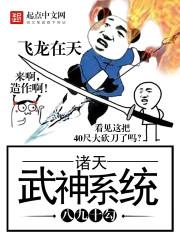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棋魂的小时光 > 第78章(第2页)
第78章(第2页)
他不会就此认命的。
“止步在这里……那就太可笑了。”
一边做着完全认命的事情……找寻着脑子里出线的那些片段,感觉就好像是对话中的两人——从来只出现这两个人——就在这围棋的棋坛上,鲜活的存在着。
只是需要一个个去对弈,才能知道是不是自己在找的那人。
那个记忆里……不是从第三者旁观的角度,而是仿佛鲜活的存在着那些片段里,不曾消磨掉的其中一人。
另外一个——
明明说着中文,但是语气说不出的古怪。
有时候听到的日语,细细分辨,能够清楚的得知对方是个日本人……
“日本人……吗?”
嘴角挂起倨傲的冷笑。
伸展左手,伸入了衬衫的袖口,右手抓住白色衬衫的衣摆,动作细微的拉动,感觉到衣料的褶皱以及划过瘦却有力的手臂出现的纹路,随着身体自然而然的动作——
这是穿衣。
修长纤细的手指,将木质的纽扣一个个从上往下扣好。
原本□出的小腹肌肤——与脸色一样是病态的苍白——被扣子收在白色的、做工材质都是上层的衬衫里。
接着是一件羊绒的套头毛衣。
穿好后,右手的手指随意的在原本梳理好,但是因为穿衣的动作而变得凌乱起来的头发上随意的扒拉了下。
然后弯腰——顺着脚踝一路往上,经过匀称纤长的双腿,穿好黑色的西装裤子。
撩起衬衫下摆,服帖的收入黑色的裤子中,再不厌其繁的重新对着穿衣镜,整理穿上大衣的前的仪表。
这一番明显重复着、浪费时间的穿衣动作,木子清木九段,却已经穿了整整二十年。
“无论哪国人,无分性别,只要我还活在这世上一时,便不会放弃。”
再次伸出双手,将衬衫的领子强迫性的重新按着纹路压好立起后,顺手抄起本就搁在一边整齐厚重的黑色羊绒大衣——
“毁掉了我三分之一的人生,就这么想不负一点责任?做梦去吧。”
穿戴完毕,裹上白色的自织围巾。
在酒店的休息室门口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后,关门,拿好磁卡,下楼。
将双手插入口袋中,那把除了对局之前和对局中会带着的百骨扇,安安稳稳的让自己的右手食指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