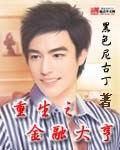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亡灵们的舞会 > 第14章(第1页)
第14章(第1页)
“他问我是否知道祖尼宗教的情况,”苏珊娜说,“我说知道不多,只是特德告诉我的那么一小点儿,”她停下来,回忆往事,“后来他问我特德有没有告诉我关于祖先精灵惩罚人的任何情况,”她皱了皱眉,“还问我是否知道任何有关精灵饶恕人的情况。”
‘饶恕?”
“他用的是‘赦免’,他说,‘如果破坏了一条祖尼禁律,是否有办法得到赦免?’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有关那事的任何情况。”她好奇地看着利普霍恩,“有办法吗?”
“我不是祖尼人,”利普霍恩说,“纳瓦霍人对祖尼宗教看来不会比一个白人对日本的神道教了解得更多。”
“那事似乎对乔治很重要,我看得出来,他老是谈论那事。”
“饶恕他吗?他有没有告诉你谁需要被饶恕?是他吗?还是欧内斯特?”
“我不知道,”苏珊娜说,“我想是为了他的,为他自已的,但也许是为欧内斯特的。”
“有没有任何要饶恕什么的暗示呢?是一种……”利普霍恩停住了,竭力想找个准确的字眼,那不会是罪行,可能会是亵渎吗?他让那句子就这样悬着,换了个说法:“他有没有说过发生了什么冒犯祖先精灵们的事?”
“没有,我当时也很想知道,可那看来不是提这样问题的时候,他那时感情激动,非常匆忙,我以前从未见乔治这么匆忙过。”
“就这样地取走了一些鹿肉,”利普霍恩说,“他取走多少?还取走些什么别的东西?”
苏珊娜脸红了,把满是污垢的卫生衫长衣袖拉下来盖住她的指关节。
“他没拿走什么,”哈尔西说:“他要来着,但没得到。据他行事看,我揣测他是逃避法律制裁什么的。住在这里的人与逃亡者是不合作的,不帮助也不教唆,啥他妈的也不给,以免给警察口实来跟我们争论不休。”他向利普霍恩露齿笑笑,”我们是守法户。”
“所以他没带什么食物就离开这里了。”利普霍恩说。
“我劝他带上我的旧上衣,”苏珊娜说,她盯着哈尔西看,带着一种既挑衅又害怕的古怪表情,“那是件人纤质料的旧棉袄,肘弯部有个孔。”
“他是什么时间离开的?”
“他到此是刚刚下午,我想他十分钟后就离开了——可能是三点或三点十五分。”
“他没说过他曾到哪里去吗?”
“没有,”苏珊娜说,有些犹豫不决,“真的没有,我敢说。乔治有点象是个疯狂的小仔,满脑子怪念头,他说他可能得离开一段时间,因为他得找精灵们。”
利普霍恩在隔开拉马-奥霍卡连特公路和纳瓦霍放牧分地的栅栏处停了车,他熄了火,打了个呵欠。他这就要走下货车、打开铁丝网门,驰向拉马。但他只是坐着,疲劳使他动弹不得。他是中午前后听到关于乔治·鲍莱格斯的情况的,而现在已经是午夜以后了。鲍莱格斯,你这小杂种,你在哪里?你睡得暖和吗?利普霍恩叹了口气,从车上爬下来,两腿僵硬,走过来打开门,又爬回货车,开车穿过栅门,又爬出来关上门,爬回货车,在尘土飞扬和砂砾中开上乡村道路。
他有些打冷颤,就把暖风门开大些。外面空气完全静止,天空无云,月亮几乎就在头顶,今夜将很冷,乔治·鲍莱格斯和欧内斯特·卡泰在哪里呢?死了吗?也许卡泰死了,但忽然又觉得不太象,没有任何人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会杀他,血也可能来自其他原因,也许今天是白白浪费了,除了血迹,没有更多情况,矮松下两平方码浸血泥土和两个小孩失踪,其中一个大家都认为有些傻,还有些什么呢?从人类学家的帐篷中偷走一些东西——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甚至还没发现丢失,还有一个象是祖尼祖先精灵的东西在月光下在嬉皮士群居村窥探。那该死的是什么呢?他又想了一遍他用望远镜看到的情景,重塑他记忆中的身影。是他眼睛在微妙的光线下把只是看来奇怪的东西看成他想象中的东西了吗?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一个大毛帽被奇怪地折射了?不可能,利普霍恩叹口气、打个呵欠。他的头由于疲乏而嗡嗡直响,他无法再集中精力,他今晚将睡在拉马小教堂里,明晨他要和祖尼警局核实材料,他们也许会告诉他夜间卡泰已经回家,承认了这是个愚蠢的胡闹。利普霍恩忽然知道解释应该是怎样的:为沙拉柯教宰了一头羊,那两个孩子贮存了它的血,用它煞费苦心地开了个玩笑,并没意识到这玩笑会令人痛苦。
在道路穿过俯瞰拉马谷地的分水岭上,利普霍恩放慢车速,拍拍无线电发报器。拉马的报务员可能早已上床,但利普霍恩仍很快打开话机。
有三项给他的通知。上尉想知道他关于小吨位货车挪用款的事件有何进展,他妻子打电话要求提醒利普霍恩,说他下午2点预约了盖洛普的牙医生;还有祖尼警察局打电话要求通知利普霍恩,说欧内斯特·卡泰已找到。
利普霍恩对无线电皱皱眉:“找到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吗?”
“让我核对一下,”发报员说:“我没拿通知,”发报员用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说,利普霍恩用手抹抹脸,强压下一个呵欠。
“找到了他的尸体。”发报员说。
第七章
星期二,12月2日,上午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