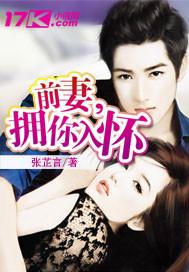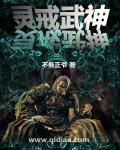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明朝重臣张居正 > 第109章(第1页)
第109章(第1页)
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消息传出,天下大哗,官民皆有怨愤不平者。
处在事件旋涡中心的张居正,并未尝到胜利的喜悦。
这是一次信心与声望上的重创。
他守父丧而不离开相位,从大局考虑,情有可原。但这样做是逆伦理习俗而动的非常之举,本应以温和、低调的手法处理,但在开始时,他过分相信皇帝的威力可以压倒舆情,&ldo;做戏&rdo;做得太过简单。当反对的浪潮爆发后,又过于惊慌失措,处理失之操切,以至步步被动,完全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到最后,只能靠高压手段扑灭舆论,从而付出了最大的道义代价。
在镇压过程中,其斩尽杀绝的做法,也引起公众的心理反弹,为政敌指责其&ldo;擅权&rdo;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在整个&ldo;夺情事件&rdo;中,张居正保留相位的好处,远抵不上失去人心的损失,并且此事对他以后的执政作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居正的门客宋尧愈在事前的建议与分析,可说是非常有远见的,可惜未被采纳。
&ldo;侧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rdo;(张居正诗《潇湘道中》)
今日位高权重的张阁老,不知还能否记起年轻时的抱负?想廓清天下,自己先清否?想为不世之才,为何偏留下了百年之憾?
因为青史无情!
任何一个英明的人物,都不能以功绩作为资本来做恶事,人们在判断一个人好坏时,用的并不是加减法,而是有一分恶,就是一分恶。这一分恶只要做了,就将永久留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你其他方面的光辉可以抵消得了的。
张居正,从此有了不能瞑目之耻!
十四、有多少雄心大业浪淘尽
【他终究不能为圣贤】
风波过后,又是百鸟压音。讨厌的人通通给逐出了视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张居正的位置,稳如磐石,来自后宫的信任与小皇帝的眷顾,一点儿没有衰减。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却有一个东西崩塌了。
在夺情风波之前,他很自负,认为自己在官场的平步青云,乃是才华超群所致。当了首辅之后,令出如山,无有阻碍,就更是为权力幻觉障住了眼。以为自己掌握的是唯一真理,以为自己是上天唯一钟情的人物,以为位居己下的其他人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所谓&ldo;不世之才&rdo;,就是指几百年出一个、甚至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物。
环顾大明浩瀚疆土,傲视天下万千苍生,谁行?谁配?
但是他忘记了,凡上天赋予一生灵以头脑,就有他的好恶,就有他的尊严。
屈居在你之下,或者因时运不佳,或是机遇尚未到。没有谁能把一个人真正看做是一尊神。
在夺情风波中,张居正的&ldo;楷模&rdo;形象被滔滔议论瓦解了。他第一次惊讶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权威,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吝自己的笑容。
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恶毒的评价加在你的身上。
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到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完美。
文渊阁往日的宁静飘然远去,张居正骤然感到自己是走在荆棘丛中。人心,不可测。不仅是门生能够反目,亲手提拔起来的下属居然也会背叛。
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
权力。惟有手中的权力,才可以让一切人俯首。他不再指望征服他们的心了,只须能征服他们的尊严。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ldo;志意渐恍惚&rdo;,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ldo;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rdo;。《明史》也说,他从此&ldo;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rdo;。
权力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就很可怕。当年十一月初一,当风波尚余尾声时,张居正就对官员队伍开始了&ldo;快意&rdo;的清洗。他以应对&ldo;星变&rdo;为理由,建议万历下诏&ldo;京察&rdo;。半个月后,吏部宣布查处51名官员,都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南京操江都御史张岳,才名本来极高,只因反对夺情而以&ldo;才力不及&rdo;而降调。
反之,对拥护一派的则尽力提拔。南京吏部尚书潘晟官声素不佳,因为&ldo;立场坚定&rdo;,反而被擢升。
张居正当年逐高拱时,尚能重用几个高拱一系的人才,并不是一律排挤,如推荐张嘉胤为浙江巡抚、张学颜为户部尚书、吴兑为宣大总督,现在则已完全失去了那种肚量。
此次清洗并非出以公心,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令见风使舵者高兴、表里如一者沮丧。张居正的今日,变成了他曾在昨日猛烈抨击过的大昏大庸者。
看别家病易,剜自身疮难。谁能逃得了这铁律?
后来到了万历十三年,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巍上疏说:&ldo;执政为了清除异己才举行闰察,众心不服,请求永停闰察。&rdo;万历皇帝照准执行,取消闰察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在这次闰察中做得太不公平。
自这次闰察后,一个以乡谊、年谊、姻亲、师门为纽带的新的官僚体系建立起来了。张居正再不想陷入朝议的汪洋大海,他要的是一群没有自己嘴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