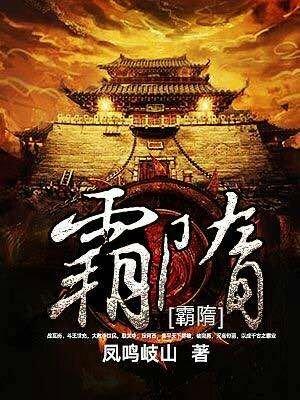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庶子逆袭重生番外书包 > 第42章 谢谢支持哦(第1页)
第42章 谢谢支持哦(第1页)
安卧家中,所有寝具都是熟悉用惯的。
疲累不堪,本该一夜黑甜无梦到天明。
然而容佑棠却辗转反侧:从枕头左边挪到右边、从上面挪到下面、从床头挪到床尾。
剿匪期间都睡得死沉死沉,可这一晚,他却做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梦:
难道是因为初次出征、精神过于紧绷?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容佑棠一时梦见鹅毛大雪北风呼啸,他艰难骑着马,拼命追赶,可前头大军却跑得飞快,转眼不见踪影!风雪迷了眼睛,他万分着急,大喊:“等等!等等我啊!”可隆隆马蹄声渐行渐远,眼前一片白色空茫。恍惚还听见有士兵说:“掉队的就丢野地里喂狼吧!”
容佑棠心突突地跳,咬牙努力追赶,冲过几丛松林堆雪后,拐弯处却猛然立着一人一马:
庆王戎装齐整,虎目炯炯有神,静静等待,威严道:“慌什么?天塌了?”
脑海中转瞬一闪,容佑棠忽又到了顺县城墙下,后有乌泱泱一大群土匪高举刀剑冲来、喊打喊杀,容佑棠却握着自己的短小匕首,急得大叫:“怎么是这个?我的刀呢?”
背后就是城墙壁,退无可退。容佑棠豁出去想:看来今日难逃一死了!爹,儿不孝,不能奉养终老,您多多保重,希望来生咱们做亲生父子、有平凡温馨的家,愿所有不幸在今生彻底了结!
容佑棠打定主意,大吼一声,握紧匕首,毅然决然朝土匪冲过去,是同归于尽的搏命架势——但他身体忽地腾空、有人抓住他的后领飞翔,瞬间回到了破败的县衙门前,耳边传来庆王的嗓音:
“容佑棠听令!你的任务是:守卫县衙。”
哎、哎——
对了,要身穿五十斤铠甲半时辰能跑十公里的人,战时才有资格上城墙,我没那体格,只能守县衙。
正当容佑棠睡梦里弯起嘴角微笑时,忽然被轻轻摇晃,并听见熟悉的慈祥呼唤:
“棠儿?棠儿?日上三竿了,起来吃饱再睡。这孩子,你梦见什么了?笑得这样高兴。”
容佑棠被叫醒,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爹。”他这才发觉自己横着俯卧、脑袋悬在床沿,胸口硌得生疼,他伸手摸索,掏出一看:
原来是斗剑玉佩。睡着后被压在身下了。
“这什么啊?模样怪有趣的。”容开济乐呵呵笑问,全然的有子万事足,他依次挂起床帐、床帘、窗帘、内间棉布帘。
容佑棠将其塞回枕头底,想了想,实话实说:“庆王府过年发的红封,压祟辟邪用的。”
“嗯,他们府里出手确实大方。”容开济顺势告知:“年前卫家公子捎回属于你的年礼,说是王府当差的都有。可我见不到你的面,就不愿意收,结果他急了,放下东西就跑了。”
容佑棠软声歉意道:“爹,都怪儿子不孝,让家里年也没过好。”
“只要你平安就好。”容开济感慨道:“有什么办法?毕竟爹养的儿子,男子汉总要建功立业、谋个好前程。若是女儿,爹反而更愁啊,毕竟你没有兄弟帮扶,到时只能招婿了。”
容佑棠利落穿衣套靴下床,回手整理被褥,乐不可支道:“招婿?哈哈哈,那幸好我不是女的,否则您得加倍发愁。”
“后宅年轻媳妇难呐,一家子一多半都是长辈,得辛苦伺候着,还往往吃力不讨好。”容开济摇头怜悯道。
容佑棠几下束好头发,跑去外间洗漱,赞同道:“爹说得对极了。我昨儿路过兴大家时,他老娘又坐门槛上骂儿媳妇了,每回就那几句话,无非‘水烫水凉、菜咸饭干’,她逢人就拉着诉苦告状,连我也不放过,兴大嫂子就躲门后哭,唉。”
“兴大成年后嗜酒嗜赌,兴大家的再贤惠也劝不动酒鬼赌鬼,日子过得苦啊。”容开济同情摇头,话音一转,坚定道:“咱们家就不同了!今后你媳妇一进门,就是内当家的,她若能干,铺子也可以交给她!你安心读书应试,争取得中为官,好歹跳出商贾一流,为儿孙后代谋个好出身。爹无能,我这内侍身份还拖累——”
“爹啊,您又来了!”容佑棠哭笑不得阻止,“咱们爷俩命中就该做父子的,家里也一直挺好,那些我根本没在乎过。世上德才兼备者往往宽厚仁善,只有小人才阴损短视,无需理会。”
容开济欣慰笑了笑,伸手帮儿子整理衣领,满怀憧憬道:“今后你成了亲,可得多生几个,不拘孙男孙女,让家里热闹起来。爹寻思着,你找媳妇门第绝不能高,免得她借势欺压,但也不能过低,门当户对最好——”
容家没有主母,爷俩都没亲戚。容开济只得既当爹、又当娘,用心抚养儿子。
“爹,您不是叫我先专心读书吗?”容佑棠讨饶提醒道。
长辈日常都爱唠叨这些。容佑棠听得多了,听完上句可以接下句,偶尔还会促狭打趣——然而他今天听着觉得有些、有些……
“这是自然!”容开济忙严肃嘱咐:“你年纪还小,理应全身心认真攻读圣贤书,切忌早早沉迷儿女情长,那会毁了精气神的。”顿了顿,容父又吐露:“这也是爹几番婉拒媒人的原因——”
“媒、媒人?”容佑棠正要开门出去找吃的,听得吃惊猛回头。
容父难掩骄傲:“自你中秀才后,就有好几个媒人上门打听,爹不想你分心,所以悄悄回绝了,也没发现有合适的。亲事不能急,须得慢慢来、仔细寻访。总之,门当户对是必须,也希望姑娘能温婉端庄、略通文墨,才能与你合拍。平心而论,世叔家最合适,只可惜严姑娘十年前就出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