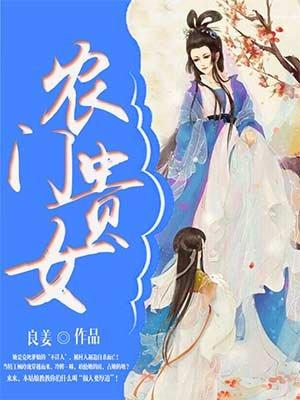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谁不说俺家乡美歌词山东话读一遍 > 第八十六章 盗墓贼(第1页)
第八十六章 盗墓贼(第1页)
当天夜里零时左右,位于凤凰岭上的村公墓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夜空中闪烁着冷光,岭上空寂的可怕。起风了,树丛中不知名的野鸟咕咕叫着,再扑棱棱飞走,旁边的野草被鸟的羽翅掠到,出一阵呼呼啦啦的回声。
微弱的星光下,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从远处“飘”了过来。黑影在距离土坡最近的一处坟茔前停下,紧接着,坟茔的墓碑处燃起一小片亮光。
就在这时,草丛里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吼声,“上!”
一时间,四面八方亮起灯光,潜伏在墓地周围的村干部一拥而上,将那个“盗墓贼”按在地上。
“照他脸!”有人将那人埋在土里的脸转过来,十几道手电光齐齐射了过去。
然后,大家伙儿都愣住了。
徐连翘看到那人闭着眼畏畏缩缩的脸,完全惊呆了,怎么,是他?!
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知谁喊了声卧槽。
太震惊了。
谁也想不到,这个不光彩的“偷供族”竟是村里o多岁的特困户徐海群!
徐连翘张着嘴,眼睛直瞪瞪盯着徐海群,赵钰见状拍拍她的胳膊,提醒她别激动。
“放开他吧。”赵钰示意大家松手。
他走上前,扶起瘫在地上的徐海群,轻声叫他:“海群叔。”
徐海群一直死死地闭着眼睛,听到赵钰的声音,他的嘴唇哆哆嗦嗦地抖了抖,眼角涌出两行泪来。
赵钰擦了擦老人脸上的尘土,柔声说:“先回吧,回去再说。”
徐海群家。
伙房。
柴火在灶膛里噼里啪啦地燃烧,火光映在徐海群沟壑纵横的脸上,将他的脸一分为二,一半红,一半黑。他的手腕瘦可见骨,黢黑的指间,夹着一支廉价的自制卷烟,烟头冒着青烟,烧了很久,他却像是忘记了一样,目光呆滞地盯着灶膛里的火苗,不说话也不动。
突然,他转了下头,僵直的目光盯着指间的卷烟,怔怔地看着。
赵钰冲上前拿下他指间的烟头,扔到地上,踩灭,他拉起徐海群的手,凑到灶膛前查看他有没有被烫伤。
还好,只是被烟灰熏了一道黑印。
徐海群瞅着面前和房顶差不多高,却弯腰屈膝细心照顾他的青年,浑浊的眼里渐渐透出一丝情绪。
他反手拽着赵钰的手臂跪了下去,“赵干部,求你给俺一条活路吧,俺不能有事,俺要是被抓起来了,俺媳子就活不下去了……”
“叔,你快起来!有话好好说!”赵钰赶紧搀起徐海群。
铁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嘟冒着泡,热蒸汽熏得人眼睛酸。
徐海群哭了。
坐在板凳上,压抑地哭诉起来。
“俺知道干这缺德事丢人折寿。俺记得俺小时候,旧社会那会儿,村里有偷祭品的,被村人抓住了,打得命都没了,俺亲眼见过的,知道怕怕,也知道这不是正经人该干的事,可俺是麽法了,实在是麽法儿了啊。俺媳子最近查出重度贫血,医生说要加强营养,可家里哪还有闲钱去买营养品呢。这些年,家里的钱全都花在俺媳子的身上,还欠了亲戚不少钱,还有翘翘,每次来都给俺塞钱。俺都一笔笔记着呢,忘不了,俺也想靠劳力赚钱,可俺身子劳坏了,下不了地,现在就是一个废人。俺媳子看俺苦,不想拖累俺,背着俺寻了几次短见,可俺舍不得啊。俺不想让她就这么走了,她跟着俺,这辈麽享过一天福,俺对不起她……”
“所以说,你偷祭品不是为了倒卖赚钱,而是为了我婶子?”徐连翘惊讶地问。
“俺干不出那种事。算上今天,俺一共偷了两次,每次都只是偷些吃的。真的,俺没说谎,俺要是偷了别的,叫天打五雷轰!”徐海群举起手,郑重誓。
赵钰拉起徐海群的手,安慰他说:“你是啥样的人,我和翘翘心里都清楚。昨天宋家坟头上掉的金项链你见了不也没捡走吗,你要是贪财的人,会这样做吗?”
徐海群抖着嘴唇,攥紧赵钰的手,“叔错了,叔做错了。”
了解徐海群偷东西的真相后,赵钰和连翘都是鼻子一酸,这都啥年代了,竟然还会生这样的事。作为村干部,他们的身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婶儿病了这么大的事你咋不跟我说呢,叔,你是把我当外人了麽?”徐连翘眼眶红红地埋怨道。
“俺欠你太多了,翘翘,俺实在麽脸再向你张口了。”徐海群惭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