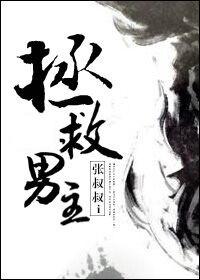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在雾中在线阅读 > 战争的遗孤(第2页)
战争的遗孤(第2页)
&esp;&esp;耳边接连传来烟丝燃烧的吱吱声,玛歌回头只能看见一团烟雾,萨克森的面庞隐晦而模糊。
&esp;&esp;玛歌很早就发现,萨克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瘾君子。他抽烟比常人厉害得多,也陶醉得多,每每坐在人群中抽烟,他犹如独自享受一场无声的盛宴。
&esp;&esp;他似乎能从香烟中汲取旁人所不能理解的快乐,几乎每一支香烟的燃烧,带给他的都是放松、愉悦和满足。但这一支,她无法判断。
&esp;&esp;“我以为您在看和母亲的合照。”玛歌如实道。
&esp;&esp;萨克森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眯着眼思索一阵,“我上次见她,是五年前。”
&esp;&esp;“这么久的分离,对于母亲来说,一定很痛苦。”玛歌望着他平静的脸。
&esp;&esp;萨克森深吸一口,“不,她已经忘记我很多年了。”
&esp;&esp;“当年,她反对我带着维尔姆参军,我答应她会保护好维尔姆。不到一年,维尔姆就死在了东线战场。我回到柏林的那个夜晚,她砸碎了为我们准备的十四岁生日蛋糕,哭着恳求我离开。”
&esp;&esp;“两年后,我被允许偶尔回家吃一顿饭。但是我知道她很痛苦,她没有办法原谅我,也不想见到我。”
&esp;&esp;“我二十岁那年,她生了一场病,痊愈之后,变得精神失常,有时见到我会高兴地拥抱我叫我维尔姆;有时会大喊大叫咒骂我是夺走一切的魔鬼,医生说我对她的病情没有好处,最好不要见面。”
&esp;&esp;“后来她完全康复,与常人无异,只是偶尔跟邻居聊天时会说起,自己曾经有两个儿子,但不幸都死在了俄国的战场上……”
&esp;&esp;他手里的烟燃尽了,伸手去够桌上的烟盒。玛歌探身帮他拿到,打开取出一支,抿在唇间,点燃后吸了一口,然后递在他唇边。
&esp;&esp;“您没怨恨过他们吗?”
&esp;&esp;这是一个尖锐而残忍的问题。萨克森咬住那支烟,竟然笑了出来:“这就是战争。难道你不恨我吗?但你还是留在这儿让我操。”
&esp;&esp;“人在支付了生命的最高代价之后,到死之前,就没有什么不能忍受。”
&esp;&esp;萨克森啪地一声关上了相册!
&esp;&esp;“我已经为这场战争,支付了最高代价。从那天起,我会杀死遇到的每一个敌人,直到我被敌人杀死的那一天!”
&esp;&esp;玛歌看着他胸前佩戴的唯一一枚勋章,漆黑的铁十字,底部标注着1914。
&esp;&esp;她忽然明白了这枚勋章的意义。
&esp;&esp;也许战争于每个士兵都有不同的意义,有人为荣誉而战,有人为帝国、为元首而战……但萨克森似乎属于最纯粹的一种,他为战争而战。
&esp;&esp;也许他并不热爱战争,可到了这种地步,他已融身其中,无法摆脱。将自己当作一种燃料理所应当地投入到这架战争机器中去,坚定走向被燃尽的终局,是他唯一的宿命。
&esp;&esp;如他所言,他已经为战争支付了最高代价。那么离开战场,他的存在将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