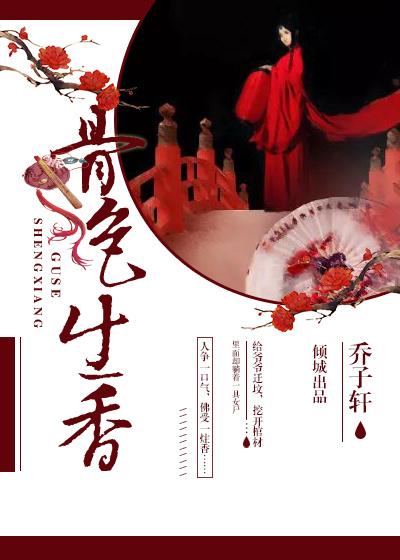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战士归乡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大强说,到营部不久就学会了,营部兄弟都抽烟,我要不抽就不算大家庭的一员了。
我说,臭小子你越来越滑头了,跟福建的独乳姑娘还保持联系吗?
大强傻笑起来,表情里荡漾着幸福无限。晏凡插了嘴,说,他何止是跟人家保持联系呀,就差把独乳姑娘从福建骗到营部再往床上按了,前不久这姑娘还给大强寄来了她亲手编织的毛衣。
大强说,晏凡你用词不当,哪是骗啊?爱,这是爱,爱情,将心比心。人家对我好,我就对人家好,人家反过来就会对我更好。她真的不错,温柔、贤慧、很懂事,每次来信都鼓励我好好训练,争取早日立功入党当干部,感觉跟母亲似的。
我说,好好珍惜吧,如今这年代世风日下,好女人越来越少了。
大强说,会的会的,幸亏跟晏凡分在了一起,每次回信都是我说他写。要是跟史迪分在一起就没这么好了,王八蛋肯定不会像晏凡这么好心地成全我们。
我告诉大强,史迪现在一连混得不错,当上了副班长。
晏凡笑了起来,说,他给我来过电话,乐得屁颠屁颠的,跟当上军委副主席似的。
大强说,哼,不过就是小人得志,没什么好骄傲的。做人不能太狡猾了,还是踏实本分的好。史迪早晚会栽的,他肚子里的阴谋诡计太多了,迟早得吃大亏。
说完,大强跑下楼去。再次上来的时候,手拎一军用水壶的米酒,非要我喝上几口。实在拗不过大强的热情,我捧着水壶喝了几口,发觉酒是热的,有些烫嘴。我问大强是不是把酒给热了,大强说酒老板刚刚酿好,我用水壶从他锅里面灌出来的……几杯酒下肚,我的情绪就上来了,告诉他们如今我在二连连他妈养狗的都不如了。
大强陪着我叹了口气,晏凡则是一副深有同感的模样,说,彼此彼此啊,现在我是一点儿希望都看不到,每天跑来跑去,感觉好像就是在给自己掘墓。你还算好,这不是已经踏上了寻找梦想的光明大道?
晏凡的话提醒了我,我决定起身奔赴县城,他们两个陪同我去了小镇。
客车上已经坐满人,没了座位。我登上客车,几位村姑见我既穿军装又背琴,羞涩地给我让座,我谢绝了她们的好意,依窗而站。大强看见了,一个箭步迈上客车,用最为蛮横的眼神把车厢里的乘客扫视一遍,然后指了指一位衣着痞塌的年轻人,语气严厉地说:
‐‐你,起来,把座让给当兵的!
痞塌青年把他的白眼珠子朝大强翻了好几翻,最终还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车开了,我坐在脏兮兮的座位上与他们挥手告别。路上,那位被迫让座的青年不停地朝我吹着口哨,我在驻地青年吹奏的充满嘲弄的音乐中思考的问题是大强已经完成了从普通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国门卫士、人民子弟兵。
第三部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破旧客车像轮船一样,在崎岖山路上颠簸了4个多小时,总算漂进县城。
我灰头灰脑地走出车站,面对路口的红绿灯和久违了的城市景象,忽然间眩晕起来。
我在地上蹲了一会儿,站起来仍觉得头脑懵懵,迈出的步伐机械得令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怀疑自己装了假肢或者腿上绑了个高跷的同时,还不停地考虑着下一步该迈哪只脚才算正确。索性,我原地踏步走了一会儿,在车站逗留旅客大为不解的目光中渐渐适应了城市里的柏油马路。
团部驻地是一座边境贸易兴旺发达的城市,国道横穿县城。国道两旁,酒店、发廊与&ldo;汽车配件&rdo;的门面鳞次栉比。&ldo;汽车配件&rdo;门前堆积着旧轮胎、&ldo;发廊&rdo;门前灯柱旋转、&ldo;大酒店&rdo;门前除了停靠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超载货车外,还有三三两两的短裙女子坐在椅上多余!谈笑风生。短裙女子的打扮很是妖冶,头发光亮,嘴唇红艳。每当货车长鸣着喇叭从国道开过,训练有素的女子就会停止交谈,拈着裙子从椅子上站起。一只手揪着裙子,露着雪白雪白的大腿。另一只手朝司机挥舞着,满脸微笑像天使。
县城大街奔驰着流光溢彩的进口轿车,好几辆汽车我连名字都已经叫不上来。就连我最为熟悉的&ldo;桑塔纳&rdo;,竟也一改清俊面孔,随波逐流地丰腴、臃肿起来。我注意了好几辆从我身边开过的轿车,里面如果不是年轻驾驶员拉了一位中年乘客,就是已过中年的驾驶员拉了一位年轻得不能再年轻的女人。
县城的姑娘比小镇上多多了,而且更像姑娘。几位衣着新潮并且透明的精巧女孩与我迎面而过,我狼狈地回过头,像不穿军装的男人一样,把她们的窈窕背影狠狠地看了又看……几经问路,我在团机关的办公大楼里见到了裴干事。说来好笑,原来裴干事就是新兵连那位把我和史迪欺骗了的新闻干事。我朝裴干事尴尬一笑,他与我打了个热情的招呼:嗬,来啦!
我们装模作样地握了握手,裴干事要我到他房间去坐,说,参谋长这几天正发愁抓不到有损我军&ldo;威武之师、文明之师&rdo;形象的典型呢,撞见你这副流浪歌手的模样,交班会上他就有例子可举了。
进了裴干事的一室一厅,我递上香烟。
裴干事从口袋里掏出&ldo;阿诗玛&rdo;,说,抽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