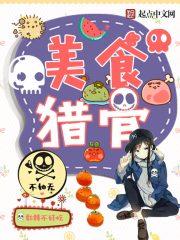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清济南府 > 第137章 山东捻乱(第1页)
第137章 山东捻乱(第1页)
坐镇济宁的僧格林沁为了剿灭乱匪疲于奔命,按下葫芦起了瓢,直忙的焦头烂额,终究是一张盖子扣不住三口锅。
眼看匪势难以阻挡,山东巡抚谭廷襄急令各县增设团练自保。刘德培与司冠平遂在博山纠集起数百人马,以“信和团”为名,与其他民团一起抵御匪患。
没过多久,捻军张敏行、刘天福部长驱直入至莱芜附近,意图攻取博山,被信和团等当地团练借助地势击退。旋即掉头攻打济南,又被官军和西城营合力挡在外围无法靠近。
捻军兵势如水,见北上受阻便转为东进,先后围攻青州、沂州未果,一部分退回了苏北,一部分攻入胶州,直取登州府。
登州外围各家民团奋起反击,但因火器落后、火药匮乏,一日之间连吃败仗,团长悉数战死,团勇阵亡八百余人。
捻军连夜进逼登州城下。当晚风大雨急,登州守军严阵以待,总兵亲自镇守南门指挥,知府冒雨巡城鼓舞士气。捻军见城内防备森严,城头又有许多巨炮,未敢强攻,僵持一夜后转而退往周边乡镇大肆抢掠。
登州城虽然兵精粮足,但胶东地区历来社会安定,很少遭大规模土匪侵袭,因而下面官民皆无防备,见到捻军来袭只能出钱求和。
捻军每到一处,先在城外烧杀抢掠,再索要银钱、鸦片、妇女等等,满意之后才扬长而去,给胶东百姓带来了巨大浩劫。
根据登州府志记载,自九月初六至初十的短短几天内,当地仅官府接获报案的死者便有七千零五十三人,被掳走男女合计八千二百零七人,遭焚毁房屋两万九千六百多间,被抢掠的耕牛骡马一万七千九百多匹,粮食衣物不计其数。
捻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数日间接连碾过黄县、栖霞、福山等地,势不可挡的向烟台进发。
当地士绅商人早已吓的魂飞魄散,纷纷集资出钱请洋人退敌。驻扎于烟台的英法两国舰队提供了部分军火,并且直接派出水兵参战,与清军共同击溃了来犯之敌。
这支捻军遭遇重创后直接返回了苏北。随着天气逐渐转冷,鲁南地区的其他捻军也纷纷南撤过冬,山东捻乱暂告平息。
然而就在这几个月之中,一些地方团练也迅速壮大了起来。刘德培与司冠平的信和团人数已经过千,等到捻军稍稍远去,他们便开始谋划跟官府算账。
九月初九,适逢博山附近举办庙会,刘德培趁机向现场百姓宣扬自己的理念,号召人们抵制官府加征漕粮。
说来也巧,恰好有差役在庙会期间提着棍棒来征粮。在刘德培的鼓动下,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将差役当场打死。
眼见群情激奋,刘德培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着大伙冲进附近村庄,将各村大户家的粮仓抢夺一空。
事情做的过了火,但当地官员畏惧团练,走形式责问了一番便没再追究,打算就此息事宁人。
刘德培看出官府软弱,于是放开手脚联合周边民团扩张声势,次月率领大队人马直奔淄川,将正在城外催粮的县衙差粮官当众斩首,要求知县取消加征的漕粮。
淄川城四门紧闭,兵丁上墙守备,情势一触即发。经过本地官员和乡绅的努力调停,知县无奈之下答应不再加征。刘德培又逼着他在城隍庙外立碑为志,方才撤军返回博山。
信和团强迫淄川县低头服软,因此受益的民众欢欣鼓舞,官府方面则是既怕又恨。等他们一走,那名被杀差粮官的家属便去省城控告,请求济南府出面缉拿凶犯。
此时陈宽已因病不理政务多时,济南知府一职由吴载勋暂时署理。他知道信和团的头目与表哥张积中之间存在联系,不愿过多掺和其中,便以“博山县民团应归青州府管辖”为由,轻描淡写的将这件事划了过去。
就在捻军搅乱山东、官府疲于应对、刘德培坐大势力的同一时期,满清帝国还发生了两件大事。
七月中旬,去年为躲避英法联军仓皇逃出京城的咸丰皇帝驾崩于避暑山庄,匆匆结束了他那被内忧外患不断困扰的短暂一生。
次月,湘军大将曾国荃指挥部队经过长期围困鏖战,终于攻下太平天国重镇安庆,在军事上彻底扭转了这场战争的态势。
湘军统帅曾国藩随后进驻安庆,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府邸设为自己的督帅行署,召集工匠开办安庆内军械所,生产武器弹药供应湘军,开始筹划收复江宁的作战行动。
正当他踌躇满志之际,慈禧、慈安两太后从承德返回紫禁城,联合恭亲王奕?剪除了咸丰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八大臣。
几天之后,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载淳正式登基即位,由恭亲王奕?辅政、两宫皇太后共同垂帘听政,并于次年启用了“同治”这样一个颇有深意的年号。
京城政治斗争尘埃落定,济南府也发生了少许人事变化。前历城县令吴载勋因处理教会讨还教堂用地一事“稳妥得当”,正式接任了济南知府一职。
新官上任,各方人士纷纷登门祝贺。魏永明与何大庚也代表西城营去送了一份贺礼,接着又去陈宽家中看望。
陈宽在山东为官多年,素以清廉勤勉着称,深得百姓爱戴。他卸去济南知府后又被任命为济东道台,但此时身体状况已十分糟糕,只能在家卧床休养。
见何大庚和魏永明到来,陈宽十分高兴,打起精神与他们开怀说笑。然而他毕竟病体虚弱,没聊多久便显得乏累了。
二人告辞返回西城营,天色已经擦黑。魏永明见何大庚闷闷不乐,知道他心中为陈宽的健康担忧,于是叫来曹老六和许宗扬等人一起吃晚饭,陪他解解闷。
大伙在公所摆起一桌好菜,喝着酒东聊西扯。席间谈及太平天国气数将尽,曹老六等人不禁神采飞扬,言语中对湘军之军容强盛颇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