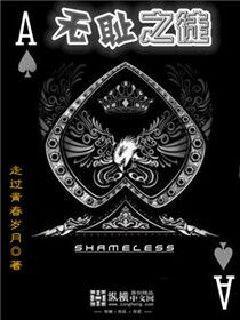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饥饿游戏3嘲笑鸟免费观看全集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ldo;训练时最好别这么说。不过能搭上你的飞机,我还是挺高兴的。&rdo;我说。
约翰娜咧开嘴笑了。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小但却十分重要的转变。我们也许不该叫朋友,盟友应该是更适合的词。很好,我需要盟友。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当我们报到参加训练时,却当头挨了一棒。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刚开始进行训练的小组里,里面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真是有点丢人。可是在实际训练中,他们却表现得比我们强得多。盖尔和其他被挑选参加战斗的人都进行了更高一级的训练。我们先做伸展运动‐‐我的伤挺疼‐‐接着是一两个小时的力量训练‐‐我疼痛难忍‐‐然后跑五英里‐‐我疼得要死。即使约翰娜一直不停地在羞辱我,我也不得不在跑了一英里之后放弃。
&ldo;我的肋骨很疼。&rdo;我向教练解释道。她是一个话不多的中年女子,我们都叫她约克战士,&ldo;上面还有淤伤呢。&rdo;
&ldo;嗯,我告诉你,伊夫狄恩战士。那些伤要靠完全自己好还得一个月的时间。&rdo;她说。
我摇摇头。&ldo;我没有一个月的时间。&rdo;
她上下打量着我,&ldo;医生没有给你治疗吗?&rdo;
&ldo;需要治疗吗?&rdo;我问道,&ldo;他们说淤伤慢慢自然就好了。&rdo;。&ldo;说是这么说,可是如果你自己建议,医生可以让你好得快点儿。可是我警告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rdo;她告诉我。&ldo;求你,我要回到医院。&rdo;我说。
约克战士没再说什么。她写了个条子,然后让我直接回医院。我犹豫了一下,真不想再错过训练了。&ldo;下午训练时我再来。&rdo;我保证说。她只是撇撇嘴。
我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二十四支针扎在我的肋部,我咬牙坚持着,真恨不得叫医生再给我用上吗啡。吗啡输液管一直在我床边,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最近我没有用,但为了约翰娜我还留着。今天,我化验了血液,验明我体内已经没有止痛剂了,两种止痛剂的混合剂‐‐吗啡还有另一支令我的肋骨发烧的东西一具有危险的副作用。医生告诉我还要忍耐两天,我说没关系。在病房的夜晚真是难熬,睡觉是不可能了。我觉得甚至可以闻到我肋骨周围的一圈肉被灼烧的味道。约翰娜在与停药后的脱瘾反应作斗争。早先,我为停用吗啡的事向她道歉时,她挥挥手表示无所谓,并且说总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到了凌晨三点,七区所有的花哨的骂人话雨点般向我砸来。可不管怎样,到了清晨,她还是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去参加训练。
&ldo;我恐怕不行。&rdo;我不得不承认。
&ldo;你行,我们都行。我们是胜利者,你还记得吗?无论有多难,我们都活下来了。&rdo;她冲我咆哮道。她病蔫蔫的,脸色灰里透青,身体抖得像一片树叶。我赶紧穿好衣服。
我们靠着胜利者的那股拼劲来完成上午的训练。当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时,我觉得约翰娜快要不行了。她面如死灰,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了。
&ldo;这只是水,要不了我们的命。&rdo;我说。她咬紧牙关,脚踏在泥地里。雨水浸透了衣服,我们在操场的泥地上艰难前行。我跑了一英里之后,不得不再次放弃。我强忍着才没把衬衫脱掉,那样冰凉的雨水就会打在我灼烧的肋部皮肤上,带走它的热量。中饭在野外吃,是泡了水的鱼和炖甜菜,我强迫自己往下咽。约翰娜吃了一半就都吐了出来。下午,我们练习组装枪支。我总算完成了,可约翰娜的手抖得厉害,没法把枪的部件组装起来。约克一转身,我就帮她弄。虽然雨没有停,但下午总算有所进展,我们开始练习射击。终于轮到我擅长的部分了。我把射箭的技巧运用到射击上。下午结束训练时,我的射击成绩全组第一。我们回到医院,刚进门约翰娜就对我说:&ldo;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们不能再住在医院里了,大家都把我们当成病号。&rdo;这对我不是问题,我可以回去和家人一起住,但是约翰娜没有分配房间。当她要求出院时,医生不批准她一个人住,即使她每天都到医院和主治医谈话也不行。我本想建议医生可以把使用吗啡的病人两个两个分配到一个房间住,可这只能让医生进一步认为她病情不稳定。&ldo;她不会一个人住,我和她住一个房间。&rdo;我宣布道。开始医生不同意,但黑密斯也帮我们说话,所以到了晚上就寝时间,我们在妈妈和波丽姆对面的房间住下,她们答应医生会对我们的病情加以留意。
我冲了个澡,约翰娜则用一块湿布擦了擦身,之后约翰娜打算在房间里四处看看。当她打开了盛着我的一些个人物品的抽斗时,她赶紧把它关上了,&ldo;对不起。&rdo;她说。
我想约翰娜的抽斗里除了政府发的几件物品,便别无其他了,她在这世上没有什么能称得上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ldo;没事,你想看就看吧。&rdo;
约翰娜打开了我的小纪念挂坠,仔细地看着盖尔、波丽姆和妈妈的照片。接着又打开了银降落伞,拿出里面的插管,把它套在她的小手指上。&ldo;看见这个我都觉得口渴。&rdo;接着她看到了皮塔给我的珍珠。&ldo;这就是……&rdo;
&ldo;是的,还是留下来了。&rdo;我不想提起皮塔。训练的好处之一就是让我可以不想皮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