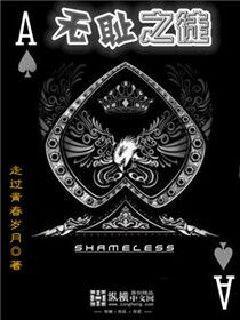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开封志怪(全三册) txt > 第24章 落发1(第1页)
第24章 落发1(第1页)
深山,古刹,斜阳,余晖,合起来,便是一种难得境界。
缁衣僧人在前,展昭牵马在后,幽静山道上,只有踏雪的马蹄声嘚嘚作响。
平日里听来,马蹄声只是马蹄声,大多数时候,心境纷扰,明知马儿在跑,却不知蹄声响在何处。
今日却不同,不紧不慢的蹄声,像极了流淌在山道上的悠扬小调,只要还在行走,这调子就洋洋洒洒连绵不绝,而一旦停下,缁衣僧人、红衣展昭还有白色踏雪,便定格为那般生动又那般清幽的山间涂鸦。
这样的景,这样的心境,展昭很多年都不曾见过也不曾有过了。
若不是此趟赴陈州公干,若不是从陈州返回时误了渡口的船只,若不是另绕山路误了投宿的客栈,若不是在山下饮马时偶遇下山汲水的好心寺僧……
想着这一连串的“若不是”,展昭的唇角扬起淡淡的微笑。
很多时候,一件事的发生,看似稀松平常,殊不知不知不觉间,某些老旧且荒废许久的齿轮开始在暗处慢慢转动,它必然会拨动或是改变某个人的人生。只是当时,你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罢了。
就如同此时,展昭在秋日斜晖掩映下的山道上安静地走着,这种安静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珍贵,让习惯于置身湍流漩涡之中的展昭有些许的醺醉。他并不知道,脚下山道的尽头处,一桩被人遗忘许久的旧事正自尘埃与沉渣中慢慢抽伸筋骨,慢慢抬起头来,慢慢等着……展昭的到来。
山道的尽头处,便是缁衣僧人所说的清泉寺。
展昭初出江湖时也曾广为游历,见过不少恢宏寺庙——南北中轴线上,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观音殿次第排开;中轴线东侧置僧房、香积厨、斋堂、职事堂、荣堂;西侧设纳四方来者的客房,晨钟响暮鼓鸣之时,别有一番泱泱气象。
清泉寺却不同,只一门一殿,殿中供结“施无畏印”的释迦牟尼佛,佛前香几,上设燃灯、烧香、饮食,东院僧房与香积厨,西院两间小小客房。除展昭与缁衣僧人外,院中再无旁人。
见展昭面有疑惑之色,缁衣僧人解释说,师父山中采药去了。
缁衣僧人口中的师父,便是清泉寺的住持。
看来这清泉寺,平日里只住持与寺僧二人,今日热闹些,多了展昭做客,还有系在山门外的踏雪。
展昭被安排在西侧其中一间客房住下,客房收拾得很干净,家什只有桌凳和床。晚饭时僧人送来了斋饭,如展昭所料,寡淡无味,好在饱腹是没有问题的。
寂寂山间寥寥古寺,时间都变得异常难挨,加上白日行路疲累,亥时初刻展昭便准备就寝。宽衣时,听到僧人打开山门的声音,紧接着便是絮絮话声,却是那僧人提起寺中有住客,另一人只是嗯了几声,语音听来甚是平淡。展昭猜是住持归来,客居于此,总要和主人家打个招呼,因此又穿衣束带,推门出去时,那住持恰好进了僧房,转身将门关起。
一出一进一开一关之间,便失了照面的机会,只隐约看到那住持的身形,并不高大,背有些弓。
展昭犹豫着是否要上前叩门厮见,最终还是息了这心思:也罢,明日见过不迟。
正待转身回房,无意中看到僧房的竹篾纸窗上映出住持单薄而佝偻的影子。展昭心中生出些感慨意味:这住持与这清泉寺一样,避缩在远离喧嚣的尘世一隅,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外界不管发生何许纷扰,于他们,都是无干无涉吧。
约莫二更时分,展昭忽然醒了。
醒来之后第一个反应,便是去握枕边的巨阙。
剑鞘冰冷,凉意渗透进掌心的皮肤,顺着身体里的经脉一路沿行,直达心脏。
屋里……似乎……有人。
这一生中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刺客夜半入室的时刻,但没有任何一次如今次般恐惧。
以往,即使是在睡梦中都保持高度的警觉,一有风吹草动,久历江湖养成的敏锐直觉会第一时间唤他醒来,救他性命。
这一次却不同。他睡得那般熟,无知无觉,直到那种让人窒息的压迫与恐惧近在肘边,他才蓦地惊醒。
若此人是刺客,自己的先机已失。
因此上,展昭紧紧握着巨阙,静静卧于床榻,并不出声,亦不有所动作。
横竖已失了先机,不妨俟敌先动。
屋内静得可怕,月光透过竹篾窗纸,在床前投下银色的月影。
所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描摹的应该就是此刻场景,只可惜展昭没有望明月思故乡的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