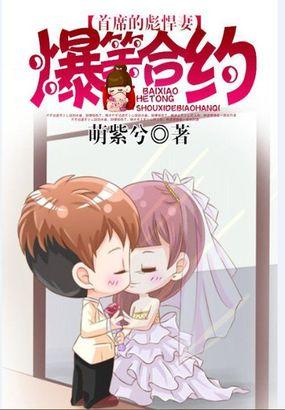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千万别跟疯批谈恋爱 长笑歌 > 第126章(第1页)
第126章(第1页)
&esp;&esp;“独横?”
&esp;&esp;谢微星学着他的样子盘腿坐下,两人仅仅隔着一面铁栅,却仿佛隔着一道跨越二十年的天堑。
&esp;&esp;“不。”程屹安反应过来,“你不是独横。”
&esp;&esp;谢微星看着他。
&esp;&esp;程屹安怆然一笑,“想让我认罪,何必叫人假扮独横?我认就是。”
&esp;&esp;不等谢微星说话,他伸出戴着镣铐的双手,在身前比划了一下,“那么多,那么多银子……”
&esp;&esp;“为官十几载,我向来清廉高洁,从未见过那么多银子,张显忠说,他已找到更好也更贱的木头做水门,绝不会出事,也已找好翁启善做替罪羊,只要翁启善一死,就算工银融成碎银一事败露,也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头上。”
&esp;&esp;“他要我与他同流合污,要我与他官官相护,谁能想到,谁能想到……”
&esp;&esp;程屹安双唇颤抖着,仿佛又回到山湾江倒灌那个清晨,他还在酒醉中数着工银,便被人摔破美梦。
&esp;&esp;“张显忠一口咬定是我指使,我百口莫辩,好在他拿不出任何证据,好在有个舞姬替我作证。”
&esp;&esp;谁能想到,他最耿耿于怀的庶族出身,竟成了一张保命符。
&esp;&esp;“张显忠必须死,他若不死,就是我同厚垒死。”程屹安眼中显露一丝阴狠,“闻廉说来探望我,实则去杀了张显忠,并做出他在狱中畏罪自尽的假相。”
&esp;&esp;“可他们却不信我,折子一张张往王爷跟前递,于是我又想到一个办法,差人来刺杀我和厚垒,这下终于有人相信,信我俩是无辜的。”
&esp;&esp;“我本以为这件事会沉入水底,永无再见之日,可没想到,我同闻廉的议事却被魏书胜听了去。”他跪坐起来,慢慢蹭到铁栅前,“是他自己撞上来的,他也得死。”
&esp;&esp;铁栅的缝隙仅有三指宽,谢微星只能看见一双眼珠。
&esp;&esp;里头盛着人类所有恶性的起源——贪婪。
&esp;&esp;“只是为了那些银子吗?”谢微星的声音从木质面具后传出已听不出原本音色,沉闷带着回响。
&esp;&esp;“你不懂。”程屹安摇头,“你不懂,你没见过,自然不会为之所动。”
&esp;&esp;谢微星向前倾身,两人的视线越来越近,“我是不懂,但我知道,那个岁高定深门一蹴鸿鹄志的程定廉,他不会做这种事。”
&esp;&esp;程屹安一怔,而后哈哈大笑着滚去地上,“岁高定深门!一蹴鸿鹄志!岁高定深门!一蹴鸿鹄志!哈哈哈哈!”
&esp;&esp;“那都是假的!”他倏地坐起身,歇斯底里,“都是假的!”
&esp;&esp;“有的人一降世便在高楼琼宇中,手握瑾瑜,身披金衣,而有的人披荆斩棘,穷极一生,却连一个薄薄的台阶都爬不上去,我又该如何一蹴鸿鹄志?”
&esp;&esp;谢微星仿佛看着一个陌生人,“可你明明说过,就算卑官野吏,就算郎前白发,也愿意报效朝堂,为百姓谋——”
&esp;&esp;“我不愿意!”程屹安打断他的话,一字一顿道:“谁愿做那卑官野吏?”谢微星怔愣。
&esp;&esp;“我也要站在高楼琼宇中。”
&esp;&esp;他的出身仿佛成了一个污点,连个寒门都算不上,全凭萧独横和陆寂对他青眼有加,才得以走到如今这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