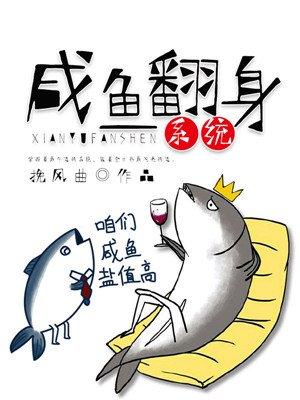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必然是我的薛榅 > 第146章(第1页)
第146章(第1页)
毕然问:“累吗?”
“不累。”
薛榅指节敲了敲脖子后方,缓声道:“替我按两下。”
毕然细嫩白皙的双手落在他脖子处,慢慢地捏了起来。她没给男人按|摩过,不知该用多大的力道,凭着感觉胡乱揉捏起来。
谁知刚按两下,就被薛榅握住手腕,轻轻一扯,带进怀里。
他嗓子有些干哑,“别按了。”
她的手很软,力道又小,按|摩跟挠痒痒似的,关键是真的挠得他心痒。
毕然歪在他怀里问:“你颈椎也不舒服吗?”
没等薛榅答话,她又自顾自地道:“听我一句劝,你明天也去做个脑部核磁共振检查。我妈一开始也是颈椎不舒服,真的,早发现早治疗。”
薛榅失笑,无奈道:“你能不能盼我点好?”
“我就是盼你好。”毕然眼睛有些热,“我妈要是早一点发现”
她没继续说下去,就这样靠在他怀里,汲取他身上的温暖。如果不是他在,她想,她已崩溃多次。
他是力量,是勇气。
过了很久,薛榅轻声问她:“要不要去车里睡会儿?”
毕然警惕地从他怀里挣脱开,下意识地抱住自己,教育他,“医院是公共场所,人多眼杂,你不能对我有这种想法。”
薛榅:
他哂笑,“你脑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
“知识。”
“生物学知识?”
毕然:
夜深了,薛榅轻轻掰了下她的脑袋到自己肩上,温声道:“那就这样睡吧。”
毕然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枕在他的腿上,身上盖着他的大衣。
而他坐着睡着了,双手抱胸,眉间紧锁。听说这样的人戒备心很强。
毕然躺在他腿上,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和心跳声,也闭上了眼睛。
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也可以被这样的天之骄子捧在手心里。
在医院的日子,仿佛与外界完全脱离开。
一周后,俞淑芬渐渐有了放疗反应,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还伴有呕吐。
谢淼送来的营养餐根本吃不上几口,有时候吃下去也是吐个精光。
眼看着人一天天瘦下去,向来乐观的蒋萍也是是一脸愁容。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能吃能喝才能有力气和病魔斗争,才有机会战胜病魔。
不过,俞淑芬本人还挺乐观,她甚至在病房里主动挑起轻松的话题,“蒋萍,给我说说你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