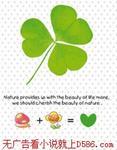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农女为商驯夫有方好种田完整版 > 第1486章 气死傅震宇(第1页)
第1486章 气死傅震宇(第1页)
傅震宇在书桌前来回走动,外孙查户部的帐目,查就查吧,怎么就扯到了他们御史台来了,气得傅震宇都不知道反驳了,更是想不出办法怎么弹劾苏义。
“不该让他当上这翰林学士承旨,皇上对他信任,什么都交给他,尤其他与他岳丈,还没有做到丞相之位,俨然就是一国丞相的样子,他这个岳丈也是事事顺着他,他到底有何能耐,连着宁相都折服。”
傅震宇呼呼吐了两口浊气,傅家父子不敢搭话,唯傅洪着实忍不住了,于是小声说道:“祖父,苏义这提议并没有错,监察御史尚且考核这些地方官员的政绩,若无管束,难免与地方官员勾结,所以为了杜绝此事,这么安排反而显得公平。”
这么近的距离,孙子说的话傅震宇自是知道了,傅震宇脚步一顿,怒目看着孙子,指着他说道:“你懂什么,官场之上哪有非黑即白的道理,你好好学学,他这是弹劾我这个外祖父,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我生气归生气,倒也没想把他怎么样,但你们再这么下去,将来必摔一个跟头不可。”
傅洪自是不认同,凭着说大实话还有错了。
傅庆松知道父亲的脾气,自是不敢接话了,于是一直低调沉默。
傅震宇叹了口气,随即看向儿子说道:“你带着洪儿送些礼物往苏府去一趟,教教他别老是揪着自个家里人不放,在官场上也不要锋茫太露,太年轻了,什么也不懂。”
傅庆松有些错愕,不是依着父亲的脾气,必想方设法弹劾的么?怎么今日却有些不同,从来只收礼不送礼的父亲也会走这一步,着实奇怪了。
而傅洪却又开了口,“祖父,此事怕是不好办,苏义从来不收礼,自打他接下户部帐目的核查,每天送礼的不知多少,皆数被苏义退回,同时反而送礼的人被苏义重点核查,祖父要这么做,那代表着祖父心虚,到时候苏义指不定还能查点儿什么出来。”
傅震宇一听气得胡子都竖了起来,“他敢。”
他有啥不敢的,这不就已经弹劾了,好在现在当政的是太子殿下而不是皇上,不然傅震宇可不是被太子责备几声的事,皇上一个眼神,傅震宇就怕了。
这一下傅震宇也是犹豫了,孙儿倒也说的对。
半晌后,傅震宇的气焰没了,说道:“这几年也怪我,苏义有几桩事说的也没有错,监察御史不能三年一任,而该是一年一任,一但上任久了,他们都会生了心思,至于监察御史的年纪不宜大,最好在翰林院里提拔,虽说他这话有私心,倒也是个法子。”
“这几年我的属下有些懈怠,我是知道的,不过一但太子殿下同意了一年一任,那将朝堂大乱的,谁又能洁身自好,一生清白的,这些初上任的翰林院才士,要么没有煞气不堪大任,要么一头热血,如苏义这样的,只会让地方官员更加乱上加乱。”
“虽然有些官员作风不好,但他们的确是当官的料,会做事,却周全,也能解决不少事情。”
傅震宇将实情说出来,傅庆松听了并不觉得什么,傅洪听着却是惊讶的站了起来,看着祖父说道:“竟然还有这样的人,祖父,你是言官之首,你该是知道的,岂能容下他们。”
然而傅震宇给孙子一个郁闷的眼神,“你太小了,懂什么。”
傅洪却是气不过,什么他太小了,他凭什么就不懂了,他跟在苏义身边这几年,与郑泽瑞三人是铁三角,-心只为百姓,为国家,从来没有半分私心。
傅震宇不想跟孙子细说,毕竟他与外孙一样一头热血,于是他看向儿子,说道:“看来我过不了几年就要退下来了,你们得做好准备,龙儿在京师营如何?卫将军可有照顾他一些?”
傅庆松一提起小儿子的事,颇有些头痛的说道:“以前在家中,文不成武不就,本以为他没啥本事,没想进了军营,倒是有些能耐,只是才有起色,他又说要去什么神机营,还一进去便半年甚至一年不得出来,我又有好几个月不曾见他了,也不知逍遥王弄出的那个神机营是做什么的,搞得神神秘秘的。”
傅震宇一听摆了摆手,“算了,他能在军营里站稳脚跟我就放心,也不指望他能有大成,倒是你和你弟弟,我现在倒是将全部希望放在你身上的,这三年之内,你必须出政绩,若不能做到户部侍郎之位,我便将你调去工部或者礼部,吏部难以进去,那边我插不上手。”
傅庆松听后点了点头,只是内心却是难受,儿子都入京为官,虽说官阶没有他的高,但他跟在外甥身边,升官自是容易,反观他不死不活的在户部混了多年。
尤其今年新调任上来的孙浦,还是宁相的女婿,一过来就成了时柏礼的心腹,将来户部侍郎之位他怕是难以到手。
礼是不敢送了,傅洪说过,一但送礼就是心虚,反而引来苏义的注意,于是由傅庆松带着儿子去苏府坐坐,套套交情什么的。
正好今个儿苏宛平也在弟弟府上,难得的看到舅舅会来,一家人在桌前坐下,傅庆松看向外甥女,只好感激的说起自家小儿傅龙去往京师营多亏她的帮衬。
苏宛平一想到表弟傅龙,她便想笑,想必表弟还在想着研制出什么武器出来好对付她这个表姐,毕竟是她当初的提议将他抓去军营的,他又是一个不服输的性子,先前在军营里的所有表现都是为了冒出尖儿,等当了官好来报复。
后来发现军机营是研究新武器的,于是自认为寻了捷径,主动向卫成请缨要去军机营,没想这一进去就沉迷了,听卫成说他还学会了自己炼铁,并与工匠们同吃同住,短短几年,早已经褪下一身贵子的毛病,越来越像军人。
傅庆松也想借机问问那军机营是做什么的,为何每次见儿子都难,一但见到了,整天赤着个膀子一点儿也没有贵子的模样,还乍乍乎乎的说要等将来向表姐报仇,也不知这个表姐怎么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