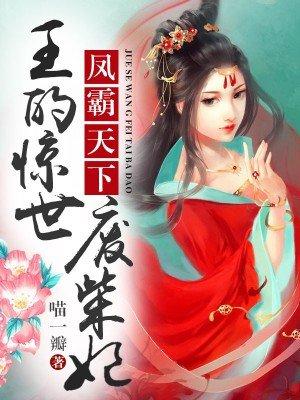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西方的没落读后感2000字 > 第33章(第1页)
第33章(第1页)
对于这一流行的西欧历史框架‐‐它使那些伟大的文化全都绕着以我们为所有世界事变的假想中心的轨道运行‐‐最恰当的称名莫过于历史的托勒密体系(ptoleaicsysteofhistory)。在本书中,我将提出一个替代的体系,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是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从分量来看,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象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古典文化,而从精神之伟大和力量之上升方面来看,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
七
&ldo;古代-中古-近代&rdo;这一框架的最初形式是麻葛式(agian)的世界感的产物。它最初出现在居鲁士(cyr)以后的波斯教和犹太教中,它从《但以理书》有关世界四纪(thefourworld-eras)的教诲中接受了一种启示录的意义,尔后在东方的后基督教(post-christian)的宗教中,尤其是在诺斯替体系(gnosticsystes)中发展成为一种世界历史。
这个重要的概念,虽然将其心智的基础局限于狭窄的限度内,其本身却是无可指责的。印度的历史甚或埃及的历史都不包括在其主张的范围内。对于麻葛式的思想家来说,&ldo;世界历史&rdo;这个表达意味着一幕独特的、最富戏剧性的戏剧,其舞台迤逦于希腊至波斯间的大陆,在这戏剧中,东方那严格的二元论世界感不是表现在同时代形而上学的诸如&ldo;灵魂与精神&rdo;、&ldo;善与恶&rdo;这类两极的概念上,而是表现在有关世界的创造与世界的衰灭之间的时代变迁的灾变形象上。
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古典文学中,另一方面在圣经(或这一特殊宗教体系的其他圣书)中得以稳固的那些要素,没有一个不出现在这一图象中,这一图象代表了(例如《旧约》和《新约》就分别地代表了)一个极易了解的对抗,如非犹太人与犹太人、基督教与异教、古典与东方、偶像与教条、自然与精神等之间的对抗,可是,它具有一个时间的意涵(tinnotation),即在这一对抗的戏剧中,一方总要胜过另一方。历史的时代变迁由此披上了宗教&ldo;救赎&rdo;这一富有特色的外衣。总之,这一&ldo;世界历史&rdo;的概念是狭隘的、有地域性的,但在其限度以内,又是合乎逻辑的和完整的。因此,它必然地只能是这一地域和这一人类所特有,不能有任何自然的延伸。
但是,在西方的土地上,在&ldo;古代&rdo;与&ldo;中古&rdo;这两个时代之外又加上了另一个我们称之为&ldo;近代&rdo;的时代,由此第一次使历史的图象获得了发展的外貌。东方的图象是静止的。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对立物,它的结果是平衡,它的转折点取决于独特的神力作为。但是,自从被一种全新的人类所采用和限定之后,它很快就变成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奇妙的变化)一种直线发展的概念:从荷马或亚当‐‐近代人可以把这些名字换成印欧人、旧石器人或直立猿人‐‐经过耶路撒冷、罗马、佛罗伦萨而至巴黎,依每个历史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趣味的不同来选用,他们可无限制地、自由地解释这一三分的框架。
这第三个时期,&ldo;近代&rdo;,从形式上看是那一系列进程中最后的和结尾的阶段,但在事实上,从十字军以后,它就一再延伸,终至到了不能再延伸的弹性边缘。尽管所言不多,这一概念也至少意味着:在此,在古代和中古以后,某个确定的东西已经开始,这就是第三王国(thirdkgdo),在其中的某处,将有一个完成和顶点,将有一个目的性的终点(objectivepot)。
至于这个目的性的终点是什么,每个思想家,从经院学者到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殊发现。对于那享有专利权的人来说,这样一种看待事物进程的方式既便当又招人喜欢,但是,事实上,他不过是复现了自己的头脑中所反映的西方精神,并用这精神来解释世界的意义。因此,正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赋予了理智的必然性一种形而上的价值,他们不仅不加认真思考就接受了&ldo;大家一致同意&rdo;的历史框架,而且将其作为自己的哲学的基础,把上帝硬拽来作为这样或那样的&ldo;世界规划&rdo;的创造者。显然,&ldo;三&rdo;这一被应用于世界时代(world-as)的神秘之数,对于形而上学者的喜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赫尔德(herder)描述历史是人类的教育,康德描述历史是自由观念的演化,黑格尔(hel)描述历史是世界精神的自我扩展,诸如此类,还有别人的一些别样说法;但是,对于它的基本设计,各人只需为那一传统的三分法想出一些抽象的意义就心满意足了。
就在西方文化开启之际,我们便遇到了伟大的弗洛里斯的乔基姆(joachioffloris)(约1145~1202年),他是第一个具有黑格尔印记的思想家,因为他抛弃了奥古斯丁(augte)的二元论世界形式,以其本质上哥特式(gothic)的智识,在旧约和新约的宗教之外加用另一名称阐述了他那个时代的一种新基督教思想,并把它们分别名之为圣父的时代、圣子的时代和圣灵的时代。他的教义打动了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最优秀的人物;但丁、托马斯&iddot;阿奎那(thoasaas),他的教义烙进了他们的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世界观(world-outlook),这一世界观逐渐地但也确然地完全主宰了我们的文化的历史意识。莱辛(lessg)‐‐他常常参照古典时代把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ldo;后期世界&rdo;(after-world)‐‐从14世纪的神秘主义教义中获取了他的有关&ldo;人类教育&rdo;分为童年、青年和成年三个阶段的观点。易卜生(ibsen)也将这一观念不折不扣地引入他的《皇帝与加利利人》(eperorandgalilean)(1873年)一剧中,在那里,他借巫师马克西姆这个人物直截了当地展现了诺斯替教的世界概念,而在1887年,他在斯德哥尔摩作的著名演讲里并没有超越这一概念向前走一步。由此可见,西方意识似乎总是急于要指出一个内在于其自身的表象中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