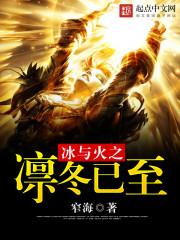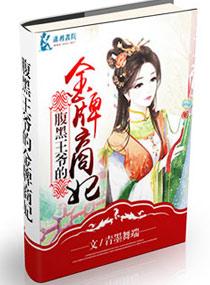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上门徒弟29 > 第41章 甩锅(第1页)
第41章 甩锅(第1页)
“自淮州水祸,百姓伤亡不计其数,受饥饿之苦的百姓更是达百万之巨。朝廷赈给捉襟见肘,流寇趁机作乱,臣实已绝望。”
“值此之际,忽闻临州同僚押运五十万石粮食相助淮州,臣感激涕零。后才得知临州运送的赈灾之粮皆出自张知白之手,他日夜不休……”
“自古商人逐利,可利一也可利十,然商人张知白心中却只有利国、只有利民。”
“他给微臣一份书信,字字恳切,为国为民之心日月可鉴。其中一语,臣至死不敢忘。他讲,无论是臣子还是商人,皆应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
‘八百里加急’的书信,当然不能只是为了歌颂张知白。
但所占篇幅属实多了些,足以看出王计生在写书信时的内心是何等激动。
大臣们相互传递书信,不乏有观之动容者,竟拂袖而泣。
不知是真心,还是做戏。
当然也有善妒者,腹诽不已。
‘好个八百里加急,明明是流寇作乱,想让朝廷下令派驻军护送其余赈灾粮食,正事没几句。张知白的丰功伟绩倒是吹嘘了不少。’
当然这种话只能在心里想,断不敢当面说出。
毕竟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再去触霉头。
龙椅上的那位,脸色可是变了又变。
“张知白买粮、运粮、捐粮已经数日,此等大事,为何地方官府没有上报?”
淮州水患是暂时解决了,可老皇帝的火却没下去。
此刻换了一个风向,继续释放。
“临州城知州余山、通州城知州李连年……都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可再看看这两人,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朝廷,还有没有朕!”
赵顺很生气,若是能早点得到消息。
何至于没日没夜地愁断肠……
何至于多次上演变脸,失了威严……
“陛下……”
殿内太监移步到了赵顺跟前,弯腰回禀。
“回陛下,内奏事处刚来的消息。此前曾收到两封书信,是来自临州城的余山和通州城的李连年,已经有些时日了。”
“多久了?”
“近十日了。”
“什么?为何耽搁了这么久!”
‘真是生不完的气,骂不够的人。怪不得张知白说做皇帝不易,还是他最了解朕的苦处。’
弯腰太监如芒在背,赶忙解释。
“陛下,书信要经数个驿站,还有提塘官、外事处、内事处……如若不是加急信件,从地方到宫内确实要耽搁上许久。”
“还不快呈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