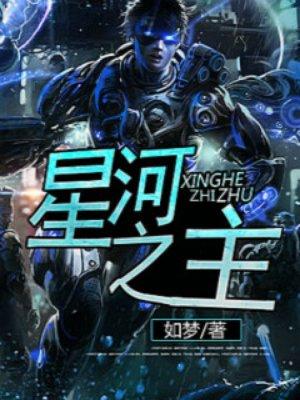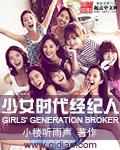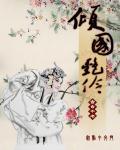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胡适留学日记汇校本 > 第30章(第1页)
第30章(第1页)
二八、叔永赠傅有周归国,余亦和一章赠行
(六月一日)
晨起,叔永以一诗见示,盖赠傅有周(骕)归国之作也。
昔君西去日,是我东游时。今日君归去,怅望天一涯。
扬帆沧海静,入里老亲嬉。若见当年友,道隽问候之。
叔永近所作诗,当以此诗为最佳矣。
余亦和一章送有周。有周为第二次赔款学生,与余同来美,颇相得,今别四年矣。有周以母老多病,急欲归去。余素主张吾国学子不宜速归,宜多求髙等学问。盖吾辈去国万里,所志不在温饱,而在淑世。淑世之学,不厌深也。矧今兹沧海横流,即归亦何补?不如暂留修业继学之为愈也。故余诚羡有周之归,未尝不惜其去,故诗意及之。诗云:
与君同去国,归去尚无时。故国频侵梦,新知未有涯。
豺狼能肉食,燕雀自酣嬉。河梁倍惆怅,日暮子何之?
二九、记历
(六月一日)
罗马初分年为十月,共得三百零四日。至nua时乃增二月,共十二月。月如吾国阴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大小相递,年共三百五十四日,后增一日,共三百五十五日(奇数吉也)。然日周天之数为三百六十五日有零(零五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故须增闰月(tercalary),间年行之。月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相递焉,于是四年共得一四六五日。平均每年得三百六十六日零四分之一,则较周天之数多一日也。于是定每十六年后之八年原定有四闰月者改为三闰,以补其差。
其后日久弊生,谬误百出,至西柴始大定历,从阳历而废月历,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年一闰,闰年增一日。时罗马七百零八年,即耶稣前四十六年也(改历之年增至四百四十五日。)西柴(julicaesar)分月之法,奇数之月(一,三,五,七,九,十一),月得三十一日,偶月皆三十日。惟二月廿九日,闰年三十日。罗马人颂西柴之功,以其名juli名第七月,今英名july者是也。
后至augt时,罗马人媚之,以其名名第八月,惟八月仅三十日,较july少一日,小人谄谀,遂移二月之第二十九日增于八月,于是七,八,九三月皆有三十一日。又以为不便,遂改九月、十一月为三十日,而十月、十二月改为三十一日。西柴之法至易记算,遭此窜改,遂成今日难记之法,小人可恨也。
西柴历(julian)虽便,然亦有一弊,盖周天之数为三六五日五时零(见上),实未足四分一之数,故每百二十八年必有一日之误。故西柴历初定时,春分节(eox)在三月二十五日,至纪元一五八二年乃在三月十一日。教皇gregory8欲正此失,乃于其年减去十日。又以太阳年(laryear)与阳历之年之差约为每四百年与三日之比,故葛雷郭令百数之年(纪元千年,千九百年之类)皆不得闰;惟百数之年,其百数以上之位可以四除尽者,乃有闰日。此法凡年数可以四除尽者皆为闰年。其百数之年如一六○○,二○○○,其百数以上诸位(年数除去两○)可以四除之者有闰;又如,一七○○,一八○○,一九○○,皆无闰也。盖四百年而九十七闰。依此法每年平均得三百六十五日五时四十九分十二秒,与太阳年差仅二十六秒,盖须三千三百二十三年始有一日之差。(摘译《大英百科全书》)
三○、《春秋》为全世界纪年最古之书
(六月二日)
全世界纪年之书之最古而又最可信者,宜莫如《春秋》(722-481bc),《竹书纪年》次之。《史记》之&ldo;本纪&rdo;是纪年体,后世仍之,至司马温公始以纪年体作《通鉴》。《通鉴》与《春秋》及《竹书纪年》,其体例同也。
三一、《大英百科全书》误解吾国纪元
(六月二日)
顷见《大英百科全书》,云吾国以帝王即位之年纪元,始自耶纪元前一六三年,此误也。前一六三年为汉文帝后元元年,盖为帝王改元之始,而非纪元之始也。《春秋》、《竹书》皆以君主纪年。《尚书&iddot;虞书》屡纪在位之年,惟不知其时系以帝王纪元否?《商书&iddot;伊训》&ldo;惟元祀&rdo;,《太甲中》&ldo;惟三祀&rdo;,皆以帝王纪年之证。《周书&iddot;泰誓上》&ldo;惟十有三年&rdo;,传序皆以为周以文王受命纪元也(参看《武成》&ldo;惟九年大统未集&rdo;句下注)。余以为此乃武王即位之年耳。《洪范》&ldo;惟十有三祀&rdo;,疑同此例。此后纪年之体忽不复见,惟《毕命》&ldo;惟十有二年&rdo;再一见耳。
三二、题&ldo;室中读书图&rdo;分寄禹臣、近仁、冬秀
(六月六日)
叔永为吾摄一&ldo;室中读书图&rdo;。图成,极惬余意,已以一帧寄吾母矣。今复印得六纸,为友人攫去三纸,余三纸以寄冬秀、近仁、禹臣各一,图背各附一绝:
故里一为别,垂杨七度青。异乡书满架,中有旧传经。
(寄禹臣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