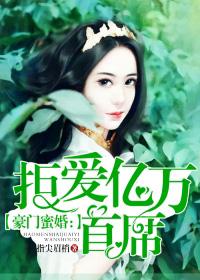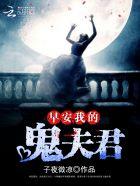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不容青史尽成灰帝都亡灵 > 第336章(第1页)
第336章(第1页)
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县城,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大文豪陶渊明的笔下,这里是所有战火纷飞下的生灵们魂牵梦萦的桃花源。与世无争的乡民们,喂马、劈柴、照顾家园,一如海子笔下的模样,在春暖花开的和平年代,世世代代做着幸福的人。
然而宋靖康二年(公元1128年)的那场悲剧却彻底终结了他们的幸福。靖康之变的一声炸雷,东北的金朝女真人似群狼一般在中原大地肆虐,无家可归的难民,抱头鼠窜的士兵,倒驴不倒架的权贵们,在金朝人雪亮的马刀下,潮水一般涌向了江南。
这事貌似和武陵没啥关系,这里是湘西,离前线远着呢,金朝人的战火烧不着武陵人的幸福生活,大宋换南宋了,徽宗钦宗换高宗了,京城汴梁换成京城临安了,可谁当家老百姓不都要纳粮缴税不是?逃难来的北方难民倒有不少,家家户户省口吃的接济着,分几亩地给种着,该过还能凑合着过,这幸福日子,怎么着都能将就着。
可武陵人到底发现,这日子,怎么也将就不下去了。
先是苛捐杂税一层层地削下来,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嘛,上下一心团结抗战嘛。然后是大量难民涌入,半壁山河都没了,要和难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嘛。接着前线战事吃紧,据说中央军地方军几下子就让人家打得稀里哗啦,长江沿线死惨了,皇上都要给赶到海里喂王八,眼看着半壁河山也要成人家的囊中之物了。乡亲们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快快奋勇支前吧。
要说武陵人的觉悟就是高,老人孩子在家,节衣缩食交着苛捐杂税,青壮年们离妻别子,雄赳赳气昂昂上前线,运气好的参加正规军,运气不好的自发组织民团,长江沿线玩命地和侵略者死磕。小小的武陵,孱弱的肩膀,支持起抗战保国的重负和牺牲,一如那年头江南无数的鱼米之乡一样,在兵火交加的岁月里,苦熬着。
苦熬到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30年),金兵的第一次南侵终于告一段落了,被追到差点跳海喂王八的宋高宗,风风光光地在临安登基当皇帝了,江淮、江南、中南战场,千千万万战死的英灵,也早就随随便便找地方刨坑埋干净了。活下来的壮丁们,被随随便便地打发回家了,皇上是只想做半壁江山主子的皇上,大臣是只想做半壁江山臣子的大臣,将军是只想保卫半壁江山的将军。南宋的红墙绿瓦间,尽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沦陷区、国耻、当战俘的太上皇、祖宗基业,人生得意须尽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吧。
当皇帝的装看不见,老百姓还看啥。各地增援前线的壮丁早就发回原籍了,半壁江山也得过日子不是,打不打仗轮不着咱操心,这苦熬的日子总算该出头了,回家继续过幸福生活吧。
可直到这时候武陵人才明白,这幸福生活,从此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当那些在前线玩命死磕过敌人,带着一身伤痕和对亲人故土魂牵梦萦的思念,被随随便便打发回家的战士们,在踏上武陵土地的那一刻,他们看到的,不是望眼欲穿的妻儿,垂垂白发的老父,更不是那熟悉的袅袅炊烟,渔舟唱晚的美景。他们看到的是烈火焚烧过的村庄,马蹄踏破的土地,混浊的洞庭湖上漂浮的尸首,残垣断壁间的累累白骨……
造孽的,不是横行北中国的金朝侵略者,武陵太远,女真骑兵的马刀伸不到这里。造孽的是一个叫孔彦舟的河南人,正宗的大宋政府军将军,还有他率领的大宋政府军,是由大宋百姓勒紧了裤腰带养着供着,指望着他们保家卫国的正宗的政府军。
这群人在历史上有个通俗的称呼‐‐乱兵。
从靖康变乱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知道像阿甘一样地跑,官跑得比兵快,兵跑得比老百姓快。跑着却也不闲着,跑到哪里就杀到哪里抢到哪里,跑一路就抢一路,碰上侵略者就连滚带爬叫大爷,碰上自己百姓就马刀挥舞滥杀滥抢。什么外敌入侵生灵涂炭,我先替你涂一遍再说。
造孽的头子孔彦舟也值得一说。他时任沿江招讨使,顶大乌纱帽的官,戎马半生也算&ldo;战功赫赫&rdo;。金兵打山东,他带头溜号,金兵打河南,他又脚底抹油,回回都是腿窜得比博古特还快。边跑边抢,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在打砸抢烧的工作战线上,他是&ldo;先进典型&rdo;。
这一回他&ldo;典型&rdo;到了武陵,富得流油的鱼米之乡,家家老幼妇孺扎堆,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活脱脱的一盘肥肉,当然是不抢白不抢。大手一挥立刻火光冲天,狞笑的&ldo;子弟兵&rdo;们钢刀挥舞,与世无争的武陵小县,在残暴的杀戮与抢掠中痛苦地呻吟,然后,就有了归乡后的战士们,不忍面对的残垣断壁和累累尸骨……
然而赚得盆满钵满得意洋洋的孔彦舟并未想到,比那些杀戮之夜的火光更冲天的,是愤怒,武陵人的愤怒。
那些在前线经历了无数次浴血奋战的民团士兵们,他们如何能面对这样的场景:无数次与侵略者血肉相搏的生死时刻,他们后方的家园正惨遭杀戮,他们牵挂的妻儿正惨遭蹂躏荼毒。做这些事情的人,不是传说中的异族侵略者,却是他们名义上的&ldo;战友&rdo;,堂堂正正的&ldo;政府军&rdo;。
这就是我浴血保卫的家园?这就是兴亡我有责的天下?这就是我们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