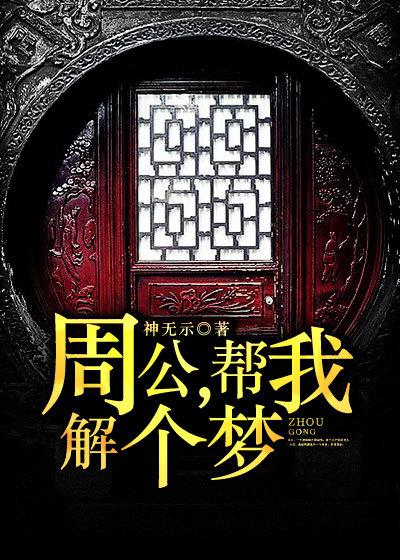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食人鱼好吃吗 > 第55章(第1页)
第55章(第1页)
&ldo;你根本想象不到的,&rdo;他说道,&ldo;不过这并不重要。我不想要这份钱。我以前对你说过,我想死在病床上。如果我干了这份差事,要不了一年我就会死去。死在街上,就像卡斯泰兰诺、波南诺和加兰蒂一样。&rdo;
&ldo;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伯父?&rdo;我问道。
&ldo;你去跟他们谈谈,&rdo;他轻声说道,&ldo;你告诉他们我老了,头脑有毛病,好忘事,承担不了这么复杂的责任。告诉他们我随时准备去养老。&rdo;
&ldo;他们会相信我吗?&rdo;我怀疑地问道。
&ldo;也许会吧。&rdo;他说着耸耸肩。
&ldo;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rdo;我说道。
&ldo;他们知道你,&rdo;他肯定地说道。&ldo;他们知道你父亲,知道他忠实可靠。他们知道你是他的儿子。&rdo;
&ldo;哦,上帝,&rdo;我说道,&ldo;我该什么时候去找他们。&rdo;
&ldo;你还有时间,&rdo;他轻松地说道,&ldo;等你整顿好电影公司的业务再说。&rdo;
&ldo;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整顿完。贾维斯的儿子们不会接受我购买他们股票的要求。&rdo;
罗科伯父露出了微笑。&ldo;我们会得到那些股票的。&rdo;他信心十足地说道,&ldo;他们用我的钱买了那些股票。钱是从我的加拿大银行出的。该银行要求他们还钱。4亿美元再加利息,贾维斯的公司拿不出来。他们已经同意把股票交给银行抵消贷款,免受惩罚。&rdo;
我们身后传来了阿尔玛的声音,我没听见她进屋。&ldo;我还放弃了我对贾维斯遗产的起诉。他们坚持要这么办。&rdo;
罗科伯父看着她。&ldo;你能从这笔遗产中得到300万。如果这一切妥善解决,你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佣金。&rdo;
&ldo;我想要500万。&rdo;她说。
他笑起来。&ldo;你可真是个秘鲁婊子。&rdo;
她跟他一起哈哈大笑。&ldo;我还是你孙女的母亲。&rdo;
我转身对着我伯父。&ldo;你们都很开心。&rdo;我说道,&ldo;可到目前为止我是唯一在交易中吃了亏的人。我先投进去8500万现金,后来又投进去4亿,到现在我一个子儿也没收回来。&rdo;
罗科伯父把目光转向我。&ldo;如果你不放心,我明天上午第一件事就是把钱给你。&rdo;
&ldo;罗科伯父,&rdo;我一边摇头,一边说道,&ldo;你知道,明天上午我就走了。我必须凌晨5点离开,回去参加上午8点钟的会。&rdo;
&ldo;那么等你回到洛杉矶时我把钱寄给你。&rdo;他说道。
&ldo;可以。&rdo;我说道。我知道明天他不会把钱寄给我。那不是他的做法。
&ldo;我是说话算数的人。&rdo;他从容地说道,&ldo;当年你想用钱做生意,我把钱给了你。这次你也会拿到钱的。&rdo;
&ldo;算了吧,&rdo;我说道,&ldo;我才不在乎能否拿到钱呢。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一家人。&rdo;
他点点头。&ldo;家族。这才是至关重要的。&rdo;他看了看表。&ldo;10点了,&rdo;他说道,&ldo;我们能在费城台得到消息。&rdo;
他转动椅子,在遥控器上按了一下,大电视开了。播音员的声音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激动。&ldo;就在我们今晚开始播音之前不到20分钟我们获悉一名费城黑手党党魁下轿车去他最喜欢的饭店吃晚饭时遇刺毙命。&rdo;画面突然从广播员的面孔转换成那个被谋杀者的面孔。广播员还在就这一事件进行报道,但罗科伯父已经不感兴趣。他关掉了电视机。
我看着他。他知道我已认出了那个人。他今天早些时候曾在罗科伯父的办公室里。&ldo;怎么回事?&rdo;我问道。
伯父耸了耸肩。&ldo;我对你说过,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没有人喜欢他,早晚会有人把他干掉的。&rdo;
我沉默了一会。&ldo;这就是他们想让你控制的社会吗?&rdo;
&ldo;我说过我控制不了,&rdo;他说道,&ldo;这正是我想脱身的原因。&rdo;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ldo;我得上床睡觉去了,&rdo;我说道,&ldo;明天一大早我就得起身。&rdo;
阿尔玛微笑地看着我。&ldo;我还以为我们能有时间聊聊呢。&rdo;
&ldo;会有时间的,&rdo;我说道,&ldo;但明天我必须为你的公民申请去见博福特参议员。&rdo;
我弯腰亲了亲罗科伯父的面颊。他的手指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脸。&ldo;睡个好觉,&rdo;他说道,&ldo;我爱你。&rdo;
&ldo;我也爱你。&rdo;我对他说道。我知道他对此深信不疑。
我也吻了阿尔玛的面颊。&ldo;晚安,亲爱的,&rdo;我说道,&ldo;你女儿很美。&rdo;
&ldo;谢谢,&rdo;她说道,我让他们继续留在起居室里,便独自下楼去招待客人的卧室。
客人卧室共有4间,我的那间是大厅尽头的最后一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最好的一间,既宽敞,又在大厅的角上。房间的另一端有一个朝阳台的落地长窗,阳台顺楼延伸从其他各间卧室的窗下经过。我只穿了一条弹力短裤,在床上伸开四肢,便把灯关掉,我无声地咒骂着。尽管窗户上挂着遮光窗帘,仍有光线从窗帘的缝隙间泄进来。窗外木板路上洋溢着太多的拉斯维加斯的气氛。我转身面对墙壁,背朝窗户,不一会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