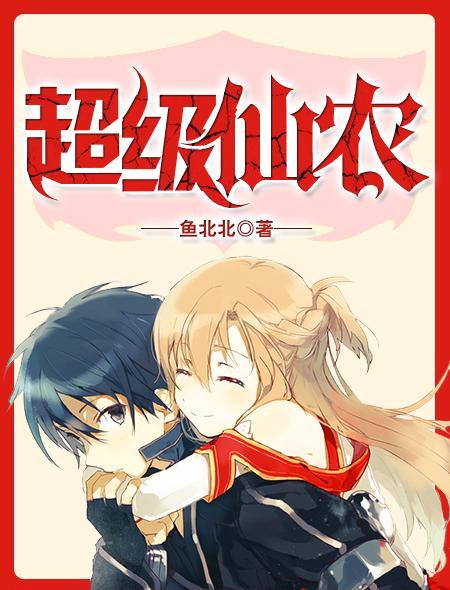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替身医生 > 第一卷 第5章 一夜情毒生死交叠(第3页)
第一卷 第5章 一夜情毒生死交叠(第3页)
趁着他低头愣神看着深入肩胛的白刃,温时颜趁机从他身下逃开,缩到角落。
应该把匕首拔下来才对,何至于现在她又处于劣势。
正懊恼,梁绛接下来的举动让她呼吸一窒。
只见他抓住匕首末端,又狠又缓慢地扭转。
极端的痛苦让他找回了属于‘人’的自己,他额头的汗大颗大颗往下掉,整张脸扭曲狰狞,嘴角却是抑制不住地咧开。
这不能称之为笑,是濒临疯癫而产生的快感。
自残?
他宁愿自残……
温时颜咬紧下唇,强迫自己不要心生怜悯。
相比于曾经自己拜他所赐的伤害,他现在所受的一切,不过九牛一毛罢了。
梁绛喘息着,血液不断地从伤口中滴落,狼狈又凌乱。
他好似压制住了部分**,视线再次转向角落的人。
温时颜防备地想要握住些什么,可手能伸到的地方,除了毫无攻击力的柔软被褥,再无其他。
梁绛双眼失神片刻,反应过来后咬破舌尖,强烈的刺激让他不敢乱看,更不敢闭眼。
他用力将被褥扬起,兜头将温时颜遮盖严实。
做完这些,立马翻身下床,脚底的虚软绵弱让他几乎支撑不住趴在地上,好想像疯狗一样行龌龊之事。
梁绛甩了甩头,汗水从发梢打到脸上,就像火苗点燃。
不行……
温时颜掀开被子一角,慢慢挪动到床尾,拿到窗台前的花瓶。
这东西就算砸不死他,也能让他在晕厥中失血而亡。
烛台下的影子渐渐拉长,一团黑色延伸到梁绛的头顶。
“阿……颜。”他突然出声,嘶哑得不像话。
温时颜骨节泛白,她犹豫两秒,决定不回应。
手臂高高扬起。
梁绛背着身,半跪着,“别怕,我……”
温时颜往下砸的动作顿在半空,一滴眼泪从下颚滴落。
就在这时,大门被猛地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