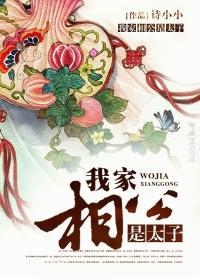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南方有令秧全文txt > 第21章(第1页)
第21章(第1页)
这是他的妻子无论如何不可能明白的。
不,他倒不是觉得男人的事情用不着跟女人解释‐‐除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他不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真有什么天壤之别。天下之大,不过只有皇上一个男人。满朝文武匍匐在天子脚下,还不是个个都像怨妇。都说为着江山社稷,不能说全是假的‐‐施尽浑身解数以博得皇帝的信赖倚重,战战兢兢地证明自己的忠肝义胆,皇帝偏听了佞臣便声泪俱下乃至以死明志‐‐史书里早已写尽了所有这些阵仗,仿佛真在竭尽全力跟天子一道演一出《长生殿》,只要唱好了天子身边的那个旦角,江山社稷从此就安稳了,就成了一只千年老鳖,为他驮着坟前那块碑。反正那块碑上,镌刻的都是煞有介事的文字,他们在朝堂上被当众褪下裤子廷杖得血肉模糊的事情,是不会写出来的。能在天子面前做成男人的臣子,千百年也许有那么寥寥二三人,但是谢舜珲不可能。这些话,岂止是不能告诉他的发妻,谁也不能告诉,只能烂在肚子里,天知地知。也只有天地,不在乎江山究竟是谁的。天地有大美,想不起来追究这么无足轻重的事情。
他家的大门终于浮在了石子路的另一头,替他驮着书的小厮语气还有点不舍:&ldo;谢先生一定要常来咱们府里串门呀,谢先生这一走,还真觉得府里没什么意思呢。&rdo;这帮油腔滑调的孩子,倒是会讨人喜欢,他自然是痛快地打赏了他,让他回去的路上自己买酒吃。
回到自己家,他一向睡在二楼的书房。书房就是有个好处,进来添茶倒水的丫鬟会告诉妻子,说他在看书‐‐他身旁的每一个丫鬟都是妻的耳目。他想象得到,她听了之后会撇撇嘴,道:&ldo;不过是看那些没用的闲书罢了,又不钻研什么正经学问。&rdo;不过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对&ldo;书&rdo;这样东西总是存着点本能的敬畏。至少知道他看书的时候,她不哭。
在家里的日子,常常能收到蕙娘的信。蕙娘总是需要一个唐府之外的人跟她闲话点家常,更何况,他们如今已成同盟。蕙娘的字不算好,不过讲起事情来倒是语句活泼,事无巨细都津津有味:云巧在六月末诞下了一个哥儿,辱名当归,上苍保佑唐家终于又有了儿子,只是这苦命的遗腹子此生没机会看见父亲;川少爷的新妇脾气委实古怪,跟府里上下都相处得不好,并且眼里没人,对夫人的态度也一向冷淡,也不知道娘家的父母究竟是怎么教的;上一次他给老夫人泡的那种药酒的确管用,老夫人最近安静了许多,若以后再得着什么好用的偏方千万记得写给她;他临走前提起过汤先生写的《紫钗记》,终于想起来她的确曾经看过,只是另有一出戏的名字叫《紫箫记》,她混淆了二者所以一时没能想起来,汤先生以后若是再写了什么,要告诉她;夫人的身体最近不大好,让人担心,连翘那丫头伺候得倒是周到把她调来夫人房里是对的……好几封长长的信,提及令秧的,却只有这短短的一句&ldo;欠安&rdo;。
他明白,蕙娘也不知道,提起令秧的时候,该说些什么好。
头一次看见她,他便觉得,这位夫人是从王江宁的七绝里走下来的。&ldo;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rdo;她就是那样的少妇,脸上还有的天真烂漫像蝴蝶那样绚烂地扑闪过去,即使她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寡妇,即使她眼睛里全是哀伤和惶恐‐‐她本人还是那抹陌头杨柳色,挡都挡不住的亮光。那一瞬间他心里其实在想:唐简虽说官场失意,可在&ldo;女人&rdo;这回事上,倒是占尽了风光呢。这世上,还有什么比娶到一个&ldo;悔教夫婿觅封侯&rdo;的女人更令人艳羡的?
掌灯的时候,他刚刚看完蕙娘最近的一封信,这封很短,也许是写了一会儿便被管家娘子打断了,之后也没心思接着写,便糙糙收尾拖人带了出去。只说新添的小哥儿当归真是乖巧煞了人,夜里都不怎么啼哭,好像知道带他的人不易,从出生就懂得给别人行方便。最令人担心的依然是夫人,大夫总是怕她会滑胎吩咐尽量卧床,她便像个绢人儿那样整日躺在被子里就像是没有声息,话也几乎不说,大夫又说是忧思郁结住了气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估计这一次拜托的信差耽误了,看看落款的日子,从休宁送到歙县来,竟然耽搁了二十多天。
他的书童静悄悄地自己进来了,谢舜珲并未唤他,不过他从不会因为这个怪罪。听得出,轻轻的脚步声停顿在那嵌螺钿的座屏旁边。他头也没回,笑道:&ldo;锄云,你这孩子越来越没个正形了,倒像只猫。&rdo;
&ldo;锄云这名字还是先生给起的呢,只怕以后用不上了。&rdo;这声音淡淡的,把他惊得猛然回头,锄云端着盏灯,站在阴影里。这孩子向来清瘦,灯光把他白皙的脸映得暗了,却益发显得嘴唇红润。
&ldo;什么意思?&rdo;他冲他挥挥手,&ldo;你靠近些啊。&rdo;
&ldo;先生一去一百多天,也不带着我,怕是用不到锄云了。&rdo;他将灯放在了炕几上,自作主张地在卧榻上坐下了。
&ldo;不要总说这些孩子气的话。&rdo;他蹙了眉头,把笔搁在那方传了很多代的龙尾砚上,&ldo;我到表妹家里是去帮忙的,中间还办了场丧事,人家家里剩下一屋子孤儿寡妇,凄凉得什么似的,带着你岂不是叨扰人家,没这个道理的。&rdo;
&ldo;我是来跟先生辞行的。&rdo;锄云幽幽地看着他,&ldo;先生不在的这些日子,太太要打发我走。我也明白,太太看我不顺眼不是一天两天了。先生前脚出去,太太后脚就撵我。是我百般叩头央告,说我只想等先生回来以后跟先生辞了行,太太才准了。昨儿晚上太太又说了,先生回家已经有些日子了,我若再不走就差人捆着我出去……&rdo;两行清泪终于挂在锄云清秀的脸上,身子一滑,就顺理成章地从卧榻上跪到了地上去,&ldo;侍奉先生一场,是我的福气。只盼着先生能记得锄云,哪怕此生不复相见了,锄云走到哪里都为先生祝祷着,求菩萨保佑先生平安康健。&rdo;
他把茶杯盖子重重地掷到桌面上,盖子被震得打了个旋,磕飞了一个角,像是魂飞魄散了。锄云伸出手在脸上抹了一把:&ldo;先生快别这么着。叫人听见了传到太太耳朵里,锄云可就罪该万死了。先生不用替我担心,太太给了我盘缠,我给家里去信说是我自己要走的。&rdo;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走到锄云面前,蹲下道:&ldo;你起来吧。&rdo;
锄云眼睛通红地笑了:&ldo;先生,你这样蹲着,我倒起来了,成什么话?&rdo;笑着笑着,又悲从中来,深深叩了个头,泪珠滴在地板上圆圆的两个水印,&ldo;锄云从此别过先生,出了这个门,往后&lso;锄云&rso;这两个字便再也没人叫了。&rdo;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不敢再看匍匐在那里的锄云。他对类似这样的场面原本就是刻骨地厌恶,看到锄云的眼泪在地上滴出来的那几颗圆印子,他不知为何,不忍踩着它们走过去,可心里看着也觉得有种类似肮脏的不舒服。他听见锄云已经起了身,在理身上的衣服,布料抖动的声音闷闷的。他问道:&ldo;你回家以后有什么打算?&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