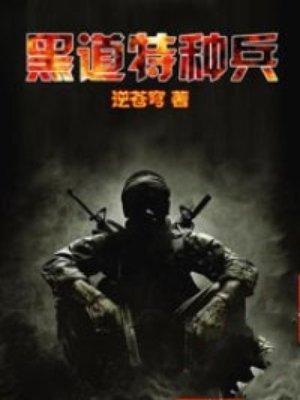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南方有令秧全文txt > 第60章(第1页)
第60章(第1页)
令秧无奈地笑道:&ldo;一天到晚神迷鬼道的,又不知在作什么怪。&rdo;说罢站起身,跟在紫藤身后,又唤上了小如。紫藤的步子轻悄而又迅疾,为了跟上她,令秧也顾不得自己其实是深一脚浅一脚,心里不由得想起多年前蕙娘骂过紫藤像猫一样,看来是没冤枉她。唐家大宅共有五进,一个天井挨着另一个地穿过去,每个天井却都面貌近似,全神贯注地走过去,令秧就感到一种微妙的眩晕。
谢舜珲漫不经心地站在拱形的后门里面,像是态度潇洒地接受了什么人将他严丝合fèng地嵌进去。身旁还有他那匹倦怠的马。见她来了,还忙不迭笑道:&ldo;夫人这次替谢某解解燃眉之急可好?收留一个人在府里暂住几日,人命关天,夫人最是个慈悲的。&rdo;她早已看到他身后还有一辆破旧的马车,以及一个心不在焉只等着结算报酬的车夫。她走上前两三步,小心翼翼地将那马车上垂着的蓝布帘子掀起一角,即刻就像被烫着那样收回了手‐‐不用多看了,只消一眼便知道这是个巨大的麻烦。她吩咐紫藤道:&ldo;叫两个侯武信得过的小子,抬上小轿过来,把人安置在谢先生平日住的屋里就好。再把罗大夫叫来。&rdo;
谢舜珲赞许地看着她:&ldo;夫人真是大将风度……&rdo;被她狠狠地白了一眼。
这位昏睡的不速之客浑身是血,令秧指挥着小如和另一个小丫鬟为他褪去身上那套粗布衫子的时候很费了一点力气。等候着罗大夫来的工夫,令秧吩咐小如她们去厨房烧开水,自己坐在那里细细端详了这人几眼。眼睛上一圈乌青就不提了,脸上、手背上都划着血道子,血迹凝结成了斑斑点点的棕色,不过尚有新鲜的血液从里面那件白色中衣上渗出来,若是能不去端详那些骇人刺目的红,便能发现这套中衣其实非常讲究,令秧甚至都不认得这是什么缎子‐‐随后她便在心内讪笑着斥骂自己:这是人家陌生男人的衣裳,还是穿在里面的‐‐看得这么细心,也不嫌害臊。明明这屋中除了她,再没第二个清醒的人了,也还是将目光挪开,移到床前摆放着的那对鞋子上‐‐全是土,脏污不堪,边沿上还沾着些可疑的东西,搞不好是踩着了田地里的牛粪‐‐不过这鞋子的式样倒是奇怪,质料也好……这念头只是迅疾地在她心里一闪,还没来得及成形,门吱吱悠悠地响了起来,罗大夫进来了。
令秧让谢舜珲的小厮留下来给罗大夫打下手,自己退了出去。谢舜珲就坐在隔壁悠闲地吃茶,跨过门槛时她恰好听见他在跟小如说笑:&ldo;你们府里的核桃苏这些年是越做越有味道了,过几日家去的时候给我装几盒带走可好?&rdo;小如认真地回答道:&ldo;这个,我得去回过蕙姨娘,看看厨房里还有没有剩下的……&rdo;谢舜珲笑道:&ldo;就不能专门替我新做几盒么,难道我只配吃你们家剩下的。&rdo;小如涨红了脸,讲话的声调因为着急,便不加修饰了:&ldo;哎呀谢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就别总是打趣我了,夫人听见了又会骂的。&rdo;说罢,一回头,却猝不及防地看到&ldo;夫人&rdo;就静静地站在她身后,手脚都不知该往哪里放了,耳边只听见谢舜珲慡朗的笑声:&ldo;你这孩子心眼儿怎的那么实在,不过是同你说笑而已。&rdo;令秧不看小如,斜睨着谢舜珲问道:&ldo;你究竟又在搞什么名堂?就算是捅了娄子叫人给你收拾,也说个明白好让我们心里有底儿。那人,可是被你的人给打成这样的?&rdo;&ldo;天地良心。&rdo;谢舜珲无奈地长叹,&ldo;谢某本想着好久没来府上看看了,今日好不容易得个闲儿,哪知道刚刚出城,小厮说要去解手,谁承想在田地里就捡到了这个可怜人……我还费了好大的力气雇来马车,才把他抬来,夫人倒这样冤枉我,想想真是没有意思。&rdo;令秧果然不好意思起来,可为了掩饰这种不好意思,除了重重地坐在椅子里眼睛看看别处,也没有旁的办法了,只好故意加重叹息的力度:&ldo;也真是个可怜人,一定是外省来我们这儿做生意的吧。我看那双鞋子式样料子都不俗,搞不好是做绸缎生意的。莫不是遇见了盗匪……作孽,他家里人还不知道要怎样担心呢。&rdo;谢舜珲含着笑正要开口,忽然听得罗大夫在外面一面叩门,一面低声地唤:&ldo;夫人,夫人可否借一步说话?&rdo;
谢舜珲不紧不慢地起身开了门:&ldo;大夫请进来吧,谢某出去便是。&rdo;在门外回廊上悠然地踱了两回步子,又朝下看了看天井的地面上静静积起的一个小小的水洼,直到罗大夫神色慌张地出来对他微微拱手的时候,才又还了礼,重新迈进去。果然撞到令秧柳眉倒竖,满面怒容地瞪着他。她生气的样子总让他觉得分外有趣。一看见他,令秧便扬起了声音道:&ldo;你是存心想坑死我吧!我真的当他只是个过路人才做主收留了,没告诉蕙娘‐‐如今可倒好,这么大的一个麻烦是经我的手弄到家里的,这叫我如何做人呢!&rdo;还嫌不解气,又咬了咬嘴唇补充道,&ldo;你看看,如今连孙子都入学堂开蒙了,你这做爷爷的办事还这么想起一出便是一出,叫人说你什么好啊,你慈悲心肠看见人落难,那你怎么不把这太监请到你家去养伤,我到底该怎么跟蕙娘说,过几日官府要是来寻他我又该如何是好啊……&rdo;与其说骂人,她倒更像是神经质地自言自语。&ldo;夫人且息怒。&rdo;谢舜珲笑着摆摆手,不知为何,她也就听话地安静下来了。
&ldo;我起初也是真的只为着救人,没想着其余的。我也是快到府上了,才发现他是税监府的公公‐‐我不是没想过原路折回去把他带到我家,可是夫人你知道,歙县眼下正是乱的时候,听说税监府一个听差跑腿的小厮已经叫那些闹事的给打死了,连锦衣卫都伤了好几个,这位公公必定也是换了百姓的衣服趁着乱逃出来的,我怕此时带他回去又生什么事端,便想到不如让他就在休宁避一阵子,等伤好了不用夫人说话,他自己就得急着回去了。&rdo;
&ldo;你又是怎么发现他是税监府的公公的?&rdo;令秧像是想到了什么,也顾不得生气了。
&ldo;其实夫人也早就看到了,的确是这人的鞋子与众不同。那是皂靴,咱们普通百姓穿不得,只有朝廷命官才能穿的。宦官的靴子式样又略微不同些‐‐反倒让夫人以为他是开绸缎庄的了。&rdo;谢舜珲极为开心地大笑了起来,&ldo;这真是极妙,夫人就告诉府里的人他是你娘家做绸缎生意的亲戚好了,这绸缎庄的来头了不得,买卖的都是宫里内造的货色。&rdo;
令秧被谢舜珲的前仰后合弄得很没面子,只好讪讪地抢白道:&ldo;我能见过几个穿官靴的,况且,那些着官服的靴子都藏在衣裳后头,哪能看得真切。你说等伤好了送他回去,送回哪里去……你告诉我,我也好吩咐家里的小厮们。&rdo;
&ldo;只怕用不着劳动夫人家的小厮。&rdo;旁人或许会觉得谢舜珲此刻的笑容是在嘲讽,可令秧却从不这么想,只是凝神在听,&ldo;用不了几日,朝廷都会派人来寻他的。夫人只管替他诊治就是了,等他醒了一切自有道理。&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