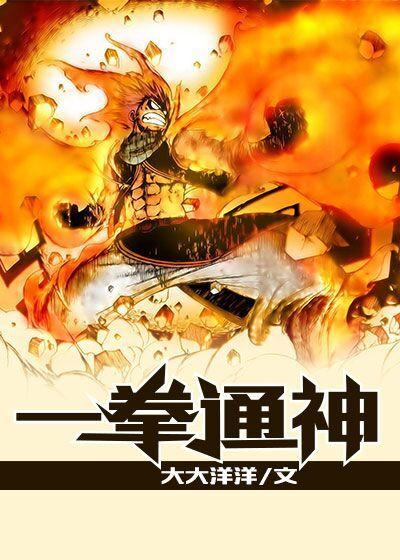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秘密花园2女主播的背景故事 > 第三零三章 徐杨丽泰(第1页)
第三零三章 徐杨丽泰(第1页)
夏沐声一滴眼泪都没掉地办完母亲的后事。
茵茵哭滴滴地拉着他的衣角跟在他后面,他没有说什么妈妈去了天上、去了你到不了的地方之类的鬼话,而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妈妈死了,她的身体会被烧成灰埋在土里,他们永远都再见不到她,但是不要紧,只要有哥哥在,茵茵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
兄妹俩是怎么相互拉扯着就长大了呢?徐若茵拉着他衣角拉了这么多年,突然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他自己,则是顺理成章地学会了假面而强势地生存。
当年徐杨丽泰微侧的脸,于夏沐声却是正面。
他避而远之许多年。但当年不太亮的灯光下,那张年轻时无比华丽、年老也不减风韵的脸,其实深深地刻在脑海中,以至于如今隔着硕大的屏风,他突然间便想到那夜的种种,他刻意封存的种种。
那位老太太居然还假作亲昵地说什么“连奶奶的面都不想见吗”?这种豪门里的老人家,她到底当自己是什么?生杀予夺的上帝吗?她竟以为他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
夏沐声并没有走到屏风里的意思,他冷冷地道:“首先我并没有奶奶,其次,我确实不想见你。”
“但你不是来了吗?”屏风里头的徐杨丽泰问。
夏沐声的确来了,事实上,他本可以拒绝进屋,他毕竟不再是那个瘦弱的少年,没有人可以轻易地把他拖去哪里。他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进来,也许,是想问个究竟。倒不是想要见徐杨丽泰。于是他实话实话:“我虽来了,却不是为了来见你。”
他停了一停:“难道不是你想见我吗?”
今天的一切透着诡异。从他拿到兰斯诚的邀请函开始,应该就进入了她设下的圈套;邀请函的聊聊数语吸引他来到京都,然后黎南桥挑了个好时间“偶见”他,他几乎是被挟持而来。能一步一步设计的这些的人,必须对他的性格有相当的了解,他有点好奇。这个人是谁。
屏风那边一片静谧。就像是徐杨丽泰突然消失了一样。
夏沐声振振衣衫,打算离开,对方既然没对话的意思。他也不必多留。
在离开之前,他多看了屏风一眼。就因这一眼,他无法轻易脱身,因为屏风边上。徐杨丽泰无声无息地走了出来。
同记忆中的那个华丽而风韵犹存的脸几乎无甚差别,只不过头发全白且多了几道再无法掩饰的皱纹。徐杨丽泰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位七十五岁的老太太。她的银发一丝不乱、服服贴贴地盘在脑后,身穿深紫祥云暗纹丝绒长旗袍,身材依然很好,面上水波不兴。她悄然地站在那里,自然便有一种旁人无法忽略的气场。
夏沐声傲然直视,毫不闪躲。徐杨丽泰却是目光慈和:“对,的确是我想见你。”
人越老。就越是盼着身后有托,自她记起有夏沐声兄妹存在的这两三年,徐杨丽泰没少派人搜罗他俩的信息,而今孙子就站在面前,仪表堂堂、一脸傲气,看上去竟如自己年轻时的翻版,比那不成气候的儿子还要可喜。所以夏沐声的冷冰冰,她是不怒反爱,如果夏沐声急着贴过来,她反倒要思量思量了。
夏沐声对徐杨丽泰的示好一阵恶寒,他对继续呆着已无兴趣:“我尊重你是老人家,想见一面就见一面吧,我还有事,恕不奉陪。但愿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干,后会无期。”
原话是“尊重老人家”,语气上可没半点“尊重”,甚至说的都是决绝的话语,徐杨丽泰脸色微变,强强压住不快:“我这里刚泡了一盏茶,你过来陪我喝完,再走不迟。”
夏沐声脸上的冰一点都没化:“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你老人家的高档茶,我享受不起,也实在没什么兴趣。”说罢,当真转了身。
“我很喜欢茵茵。”徐杨丽泰突然说道,她的语调依旧平和慈祥,仿佛并不是在拿他的七寸威胁他。
夏沐声没回答,徐若茵已同他说明一切,她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她的选择,那还有什么可多说的?见他依然想走,徐杨丽泰又说:“我拨给她五千万,希望她能把‘月曜’带起来。”
夏沐声一怔,这件事,他从未听徐若茵提过!
徐杨丽泰显然很满意他反应:“怎么,茵茵没告诉你吗?”
夏沐声转回身:“你到底什么意思?如果旧事重提,趁早死了这条心。我早就给过你答案,我自姓夏,和你们姓徐的没半毛钱关系。”他冷笑了一声:“对了,你想要有关系也行。马上把现在的那位徐夫人赶出家门,将我母亲的灵位迎进门,补她应有婚礼、应有的身份。”
徐杨丽泰的脸色沉了下来:“放肆!”
夏沐声戾气既起,哪里还怕老太太放脸:“可惜这位徐夫人的娘家同某些政要人物关联紧密,既然娶进来,怎可能再推出去?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有‘七出’之说。”他这句话说得有点过分了,明摆着是讥讽那位徐夫人无出,而徐杨丽泰想让他兄妹回徐家同时还得供着那位徐夫人实是可笑之极。
德高望重的徐杨丽泰已有多年未被人如此挤兑,一丝寒气掠过脸庞,但她马上压下了怒气:“小孩子口不择言,我老人家不和你计较。今天找你来,是因为听说你公司最近遇到了不少麻烦。”
夏沐声倒也佩服她的冷静:“就算是再大的麻烦,也不饶你费心。”
徐杨丽泰直截了当地道:“我想和你谈合作。”
她提“合作”是种聪明的说法,至少比咄咄逼人的“我‘天启’能轻易将你的困局破解”来得好接受,因为不那么像“施舍”。夏沐声怔了怔,道:“合作是双方面的,我没有同你合作的意愿。”
徐杨丽泰眯起眼:“何必这么急,何妨听听我的条件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