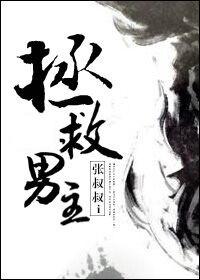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鱼汤面条有营养吗 > 第16章(第1页)
第16章(第1页)
但他最好拿捏与把握,因为他也恨她,恨意味着在意,难忘,鲠在心底,有一席之地。
所以在包厢里重遇他的下一刻,这个初涉销金窟的年轻男人,就成了她临时决定的最佳猎物。
在男人的世界里,性可以是赏,也可以是刑。她以身为饵,迎合他年轻气盛的掌罚与轻狂。
果然,他主动光顾她阴潮的洞窟,在缠斗中与她共同陷落。
自以为是的屠龙者再遇恶龙。
终成恶龙。
作者有话要说: “屠龙者终成恶龙”
昨天文下一位读者说的,我好喜欢这个形容
☆、13
张其然一直在这里待到了快早上。
薄曦透入房间时,他才发觉时间流逝如斯。
当然,他也没预想到自己会待这么久,毕竟只跟季惊棠做了两次。
第一次她被他发泄得像个处女,娇弱地呼痛;第二次,他带了更深程度的报复与征服,她满眼通红,看起来极易欺负。
按理来说,她早应游刃有余,但女人的表现并不像熟练工种。肤色是一览无余的洁净,还泛着莹白色泽,有如不见天日的深海珠,从未有人开采,直到他留下毁灭般的践踏印记。
结束后,他就躺在床上,也不抱她,兀自闭目养神。
她贴过来,他就躲,不耐烦地皱眉。
她再贴,他还是避。
第三次重复这个举动时,他忍无可忍,把季惊棠掐进臂弯里,骂了句骚货。
女人看起来心满意足,手指在他胸肌上抚摸,他也没拿开,并发现自己对她的依恋不是那么抗拒。
大概是性爱削弱了他的抵御值,张其然分神地想,或许也归咎于季惊棠踩在他审美点上的长相。
但她又像水蛭一样滑腻恶心。
这种矛盾的判断在他心头盘旋,似一只秃鹫在高空振翅不定,腐肉恶臭,却能能调动他本能的物种取向。
美丽的水蛭忽然打断他思路,娇娇问:“你给我送外卖那次还是处男吗?”
张其然来缓慢掀起眼皮:“你觉得呢。”
季惊棠扬眼:“我猜是。”
张其然说:“不是。”
他问:“为什么这么猜?”
季惊棠说:“你那会看起来好纯。”
她搓抚着他左脸,瞳仁水汪汪的,沁着一种古怪又诚实的爱怜:“比现在黑,很容易脸红,眼睛好亮的。”
张其然唇一扯:“记这么清楚?”
季惊棠也奇怪:“对啊,我怎么记这么清楚,可能太讨厌你了,见过一次就忘不了。”
张其然哂笑着:“不是送外卖的?”
“张其然,”季惊棠连念三遍,嗓音好像指缝里流出去的细细沙粒,磨得人通体舒适:“张其然,张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