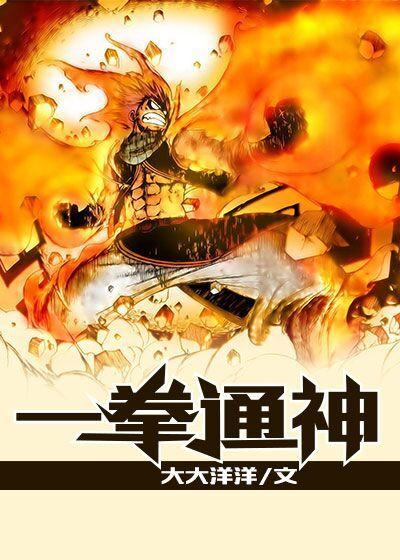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沙德维尔的暗影三部曲顺序 > 第25章(第1页)
第25章(第1页)
“您一定是哪儿弄错了,先生,”老妇面无表情地说道,“公孙寿不在这里。这儿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您在说傻话。您一定是疯了。现在,从这里出去!再也别回来。要是让我们看到您和您的朋友再出现在这里,您一定不会喜欢我们采取的方法。下一次,我们就不会对您这么亲切了。”
李一脚把我踢出门外,他用的力气很大,我没能站稳,直接滑下了前门的台阶。我一屁股摔在人行道上,痛苦地喊了一声,但受损的其实主要是我的自尊心,而非我的骨骼。
张以同样的方式把福尔摩斯也扔了出来,但相比之下,他就表现得比我更有尊严一点,在摔倒前,他就抓住了栏杆。
李发出一声嘲讽的讥笑,朝我挥了挥我的左轮手枪。接着,先做了一个仿佛要将它递给我的假动作,然后将手枪塞进自己的裤子口袋里,又在上面拍了拍,意思似乎是,“归我了”。
我挣扎着站起身,开始往回走,想从他手里把枪夺回来。福尔摩斯阻止了我。
“别去,老朋友。不值得。那不过是一把枪罢了。你随时可以再买一把。”
我刚想表示反对,但接着就明白过来,放弃了。他说得对。我对上李毫无胜算,在我看来,他的武术水平与张不相上下。要是想从他手里抢回韦布利,很可能只会招来一顿揍,甚至更糟。
为了拯救所剩无几的尊严,我只能冷笑一声,做了个轻蔑的手势。我说我希望李拿着它能玩得开心。我一点儿也不在意它。
这完全是谎话。那把左轮手枪算得上是我最珍贵的随身物品了。它不止一次救过我的性命,不只是在阿尔甘达卜山谷。我对它的感激不小于对任何一个人。
我的心与我的身体一样,痛得要命,我只能强迫自己不再多看它一眼。
*
福尔摩斯和我两人渐渐走远,将“金莲”旅馆甩在身后,我俩全身是伤,满身是泥。我十分沮丧。我觉得自己难辞其咎。要不是我不够小心,福尔摩斯本该战胜张,我们则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出那地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耻辱地被人用枪指着扔出门外。
不过,几分钟后,我将这些想法告诉福尔摩斯时,他却嗤之以鼻。
“别这么难过,我的朋友,看在老天的分上,别道歉。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让我精神了不少。另外,我们今天也不是一无所获。”
“你真的这么想?”
“我知道的。我们确实完成了设想的目标。公孙寿会听说我们的事。我们扰乱了他井井有条的生意,而它要蓬勃发展,仰赖的是谨慎和不为人知。我们让自己成了讨人厌的家伙,而我们所使用的方式,他既不能默许,也没法视而不见。倘若他在‘金莲’的奴才此刻没有跟踪我们,我反倒会有些惊讶。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活儿干得不错。”
“跟踪我们……?”
“别扭头去看,”福尔摩斯轻声说,“我不想让他们发现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说着也压低了声音,“有个中国人在跟着我们?”
“至少有一个。我不能说我完全确定,但这肯定是他们那边最有可能采用的策略。他们应该想知道我们要往哪儿去。要是我们直接往警察局的方向走,他们就会做出拦截我们的举动;而倘若我们和路过的巡逻警官搭话,他们就会去贿赂他,要不就在那警官去他们门前找麻烦之前,确保他的态度至少是中立的。公孙寿经营了这么久的鸦片馆,足以说明他做事很精明。就算他没有实际参与这些地方的日常运营,也会雇用一些足够狡猾的手下。比如说,那个老太婆,她就不是傻瓜。别被她那蹩脚的英语给骗了。她非常狡猾。”
“是的,这一点我可以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
“可以看得出?还是说你只是事后来看才这么想?”
“或许吧。”我承认道。
“那就是说,你没有留意到她的信号?”
“信号?”
“她一开始就盯上我们俩了。她意识到我们是假冒的瘾君子,于是提醒了李和张。”
“有吗?她只对他们说了没几个字。”
“但她碰了头发里插着的筷子,快速地拍了拍,三次。”
“只是调整一下角度。”
“不,是发出暗号。我才刚闹起来,张立刻就来到我的床边。他反应得如此迅速,是因为他和李都已被提醒过,我们可能会闹事,因此做好了准备。在筷子上轻拍三下的含义远比它的表象要来得更多。我猜她把我们当作卧底的便衣警察。而现在,我说出了公孙寿的名字,她知道我们的身份并非如此,肯定想知道更多有关我们的事。”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想要回头去看的强烈冲动。我们身后有脚步声吗?在这重重大雾之中,我能听到它们吗?还是说,那只是我们自己的脚步声在建筑之间的回音?知道可能有人在跟踪自己的感觉真的很怪异。翻腾的浓雾更加深了这种怪异之感。我们的影子可能跟在我们身后仅几步之遥,而我们却绝不该去看他。就算可能到头来其实是福尔摩斯判断错误,根本没有人从鸦片馆出来一路跟踪我们,但想到有个看不见的追踪者,依旧让我毛骨悚然。我们游荡着从一盏街灯的光晕中走向下一盏,而两片光明的绿洲之间,距离似乎远得无法测量,更黑暗得反常。时不时会有行人模糊的身影出现在我们前方——戴高顶礼帽和穿夜礼服斗篷的要人正从俱乐部走回家里;闲逛的流浪汉正在寻觅一处可以让他蜷一晚上的地方;女店员正为她的商品寻找最后的客户——他们每一个的轮廓都会短暂地变得立体,充满细节,而后便回到朦胧的虚无之中,彻底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