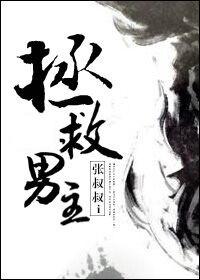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沙德维尔的暗影三部曲顺序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当我抓住司机座位的椅背,想爬上去时,我的眼角似乎瞥见了什么东西在动。是个黑色的东西,一闪而过,就在通道墙壁边上,紧挨着地面。我猜是那只流浪猫,它终于克服了对马车的警惕心,又跑回来了。那黑色的东西展开又缩回去,非常像猫科动物的尾巴。
我又看了一眼,视野中却完全没有黑猫的影子。倘若我刚才确实见到了什么东西,可能也不过就是什么无害的小东西动了一下。或许是一张废纸,被风吹起来了。
我坐上座位,拿起缰绳。拉车的马突然很紧张,发出嘶嘶的声音,用前脚的蹄子不停踩踏地面的鹅卵石。我发出安慰它们的声音。“我知道我不是你们熟悉的车夫,”我对它们说道,“你们忍一忍。我会尽量好好赶车的。”
马儿们的耳朵竖起,脑袋不时左右转动。它们似乎很想尽快上路。我拿起鞭子,正准备轻轻地往它们的后半身抽下去,此时公孙寿突然叫喊起来,那完全是一声尖叫,几乎可以算得上歇斯底里的哀号。“它们出来了,”他说,“你感觉不到吗?老天啊,它们出来了。”
我四下张望,完全看不到他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附近什么人也没有。我的身前身后都没有任何遮蔽物,此处只有我们。他怎么可能在车厢里看到我在外面看不到的东西?
但接着,一个桥墩的阴影明显移动了。
它看起来像是从通道的墙上挤出来的触须,一直探向马车。黑暗的缎带伸到马车前,而我则立刻感觉疲惫涌过全身,我的心灵和身体都变得虚弱无力。力量从我的四肢中抽离。头晕目眩的感觉席卷了我。我没法动弹,也没法去看那移动的黑色物体。鞭子在我手中耷拉下来,重得仿佛铅管一般。
那些马也受到影响,不再急于离开此地,它们似乎完全安于被套上索具,就这么站在原处,垂着脑袋。我心里有一部分知道,我必须激励自己,必须抵抗就这么逗留下去的诱惑。但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何必费这徒劳的力气?就这样看着阴影继续扩展延伸好了。我觉得它很有吸引力,仿佛催眠,在它那开花般的绽放之中,潜藏着危险的美。纯粹的空虚化作实体,探出它的触手,将我搂入它的怀抱之中。
从对面墙壁上渗出了第二片阴影,而后,从通道顶上降下第三片,它那细小的黑色手指仿佛怪异的钟乳石一般垂下。现在我已加倍、三倍地不愿逃离此处了。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了疲惫感。我甚至有些怪异地觉得,即使是被一个阴影触碰到了,也没什么不好。它们放射出一种寒意,但那种寒意带着麻醉之感,让人失去知觉,就像是醚。又好比人踏入冰湖,起初会有一阵颤栗,但随后,便是丧失感觉带来的极乐。
我处于这种麻木的状态中,几乎意识不到周围发生了什么。除了我和那些渐渐渗透的流动的阴影之外,什么人也没有。我甚至没有察觉,直到福尔摩斯设法从车厢里逃出来,爬上车夫座,坐在我身边。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十分费力,精疲力竭,简直好像他刚跑了十英里越野赛跑。他牙关紧咬,眉头也因为注意力集中而紧锁着。阴影吸走了他的生命力,但他拒绝屈服,以他仅剩的最后一点点能量与之对抗。
他从我手中接过缰绳和鞭子。他抬起鞭子抽右边那匹马的身侧。那头牲口因为鞭子给它带来的刺痛而瑟缩。而这似乎让它重新凝聚起了活下去的意志,将疼痛与前进的命令联系在了一起。它的腿抖动起来。福尔摩斯又抽了一鞭,马向前走了出去。另一匹马也想起了自己与它一致的职责,同样照做了。
就这样,马车以极折磨人的缓慢速度动了起来。
然而,阴影依旧笼罩着我们。它们黑色的触须贪婪地拍打着车厢两侧,还卷上了我和福尔摩斯的大腿。我不想直视它们的黑暗深处,但不知为何,我就是无法移开视线。我的双眼不可自抑地望向深处某个可见的形体。看不真切,就像你望向浑浊的水面,隐约能见到的某种东西——某种变化多端又包罗万象的东西,某种可怕的东西。它是不定形的。它翻搅着,卷动着,就像烟。但它又很实质化,它有光泽,肉质丰满。每一秒之间,它似乎都在重塑身形,不断演化,泛起涟漪。眼睛。它有眼睛。几十只眼睛。它们或是眨动,或是眼珠转动,或是死死盯着我。它们在望着我。它们能看见我。它们渴望着我。它们想要吞噬我。
当时我可能发出了尖叫。我记不清了。我只能记得福尔摩斯又重复了一遍让马跑起来的动作——让它们跑得快些——用鞭子一次又一次地抽打它们,而它们吃力前行的样子,就仿佛顶着一阵强劲的逆风。整段插曲都如同噩梦,在那种梦里,你竭力想从一个恐怖之物前逃走,双脚却深陷在流沙之中,无法移动分毫。
在车厢里,公孙寿已进入了彻底狂乱的状态。阴影从车厢两边沿着门缝渗透进去。他咆哮着,身子四处乱撞。我可以想象他是如何被阴影那仿若星云团一般的触须卷住,徒劳地想挣脱它们的束缚。
马车缓慢向前挪动,越来越接近通道尽头,接近那炫目的日光。与此同时,我也终于将自己的视线从隐藏在阴影中的存在上扭开了,尽管我的双眼还在不断无法自抑地想要转过去看它。那个东西是起源。它们都是从它身上延伸出来的,是它探入这个世界的肢体。它控制着它们,用它们来让它的猎物落入陷阱。它的胃口就像它的外表一般丑恶。它没有嘴,也不需要这个器官。它会吸吮。它会吸收。它会将猎物包裹。被它摄取恐怕是所有死亡中最为恐怖的,因为人的情感,人的精华,人的整个自我,都会被它纳入其中,就像水蛭吸食鲜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