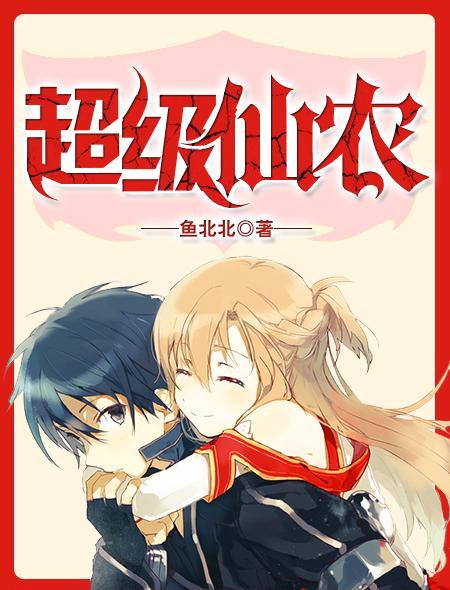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沙德维尔的暗影三部曲顺序 > 第87章(第1页)
第87章(第1页)
“好吧,这下麻烦了,”葛雷格森说道,他刚从那种狂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这些可怜的东西转向我们了,就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是我们的错。暴动即将发生。我以前见过这样的场景,在街头。私刑就是这么来的。”
此时已有不少蛇人上了高台,其他的也将脑袋转到我们的方向。如此看来,我们从一场死亡中逃脱,无非是为了接受另一场强加于我们的死亡。那些聚集起来的蛇人,主要是成年男性,也有一些女性混杂其中,他们朝我们咆哮着咒骂之词。这些话中的大部分我都听不懂,但我能听懂的部分主要是在贬低我们的衣着,因为蛇人什么也不穿,还有我们的头发,对于光秃秃的爬虫纲蛇目人属来说,头发看起来非常畸形,属于很不自然的身体特质。
“你们在说什么?”迈克罗夫特挑衅似的朝他们喊道,“你们那些叽里咕噜在我听来根本没头没尾。这样跟我们说话根本毫无意义。”
这些打算对我们施以私刑的暴民——葛雷格森的形容恰如其分——渐渐汇拢,我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近。从在阿富汗时起,这几个月中,我曾那么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那冷酷的镰刀好几次从我头顶挥过,近到足以让我感受到它扫过时带起的寒风。我一次又一次堪堪避开了它,但如今,我的运气似乎已经用尽了,而我已感觉到了它那刀刃的终结之吻。我才二十八岁。这实在算不上长寿,但我这辈子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感受过欢愉和苦难。我的生命已经够长了。只能如此结束。
一个眼镜蛇人出现在我面前,正是在地下墓穴里差点儿就往我身体里下了蛇毒的那一个。他似乎是这群暴民的领导者,所谓的雄性领袖,正不断激励着其他蛇人上前杀戮。我估计,要不是莫里亚蒂篡位,他本来应该是蛇人的酋长。而现在,他要重新夺回这个位子,而他的第一要务,就是重新着手他想做却被阻止了的事。
他愉快地嘶了一声,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上颚的凶狠尖牙。
“来呀,你这败类,”我勉强说道,“我希望你在咬我时被噎住。”
“n’rhn!”此时传来一个我极为熟悉的声音,那声音,我本以为自己再也听不到了。
眼镜蛇人猛地转过身子。
在暴民身后,出现了一个人形,他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水从湿透的衣服上哗啦啦地淌下来,在他脚边形成一汪水洼,那正是歇洛克·福尔摩斯。
*
在我已发表的两部小说《最后一案》和《空屋》中,我写到了福尔摩斯表面上死亡而后又奇迹般生还的故事。我写他是如何与莫里亚蒂教授在决战中同归于尽,并表示我推测这两个人都跌入了瑞士的莱辛巴赫瀑布,直到三年后,他才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而他假死,则是为了避免某些仍旧存在的仇敌注意到他。
就这样,我虚构了上述那些没什么不同的事件。我将它们改头换面,将场景放到了阿勒河峡谷,又用瀑布下奔腾的白色漩涡,替换了洞穴中这片表面看来波澜不惊的黑色湖泊。这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描述我以为福尔摩斯就在我面前死去,被莫里亚蒂和奈亚拉托提普拖入水底时的痛苦,还有他回来时我的惊讶与喜悦,只不过肆意更改了这些情绪后面的事实。
事实上,我们从来就没有被愤怒的莫里亚蒂跟踪着横跨欧洲,也没有福尔摩斯假扮的干瘦残疾藏书家来我家拜访。所谓的“公园路谜案”——亦即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以罗诺德·阿德尔爵士的气枪施行的谋杀——确有其事,但并不与我后来叙述的完全一致。在被一些人称为“伟大的中断”的两个故事中包含的情感是真挚的,内容却经过了大幅度的改编。
*
眼前的人正是福尔摩斯,他刚刚浮出了湖面。铁链松开的那一头缠绕在他的小臂上,他从地面上捡起三蛇王冠,捧在手里。
他对那眼镜蛇人和其他蛇人重复着同一个命令:“n’rhn!”他的声音中包含的权威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让他们听从他的要求,只不过略带惊讶。他让他们停下,而他们确实停下了。
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但就在蛇人暴民停下,面带困惑之时,福尔摩斯将三蛇王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王冠对他来说显得稍大了点,莫里亚蒂的帽子尺寸至少比他的大两个码。它戴着有点歪,靠卡在耳朵上来维持平衡。
只要他能让这魔法王冠替他发挥作用,那么一切可怕的后果都将不会发生。
我看到他的眉毛皱了起来。我看到他集中了注意力。我看到他那双灰色的眼睛失去了焦点。他咬紧了牙关。
三蛇王冠发出了光亮,一开始有些犹豫,像是在做实验。一抹绿色的光芒从它那青铜的管状轮廓线上一闪而过。它不过就像一点磷火,出现后瞬息之间便消失了。
但接着,亮光又回来了,变得更强烈,更坚定,而福尔摩斯也控制住了这顶王冠。尽管他以前从未戴过这个装置,但他依然迅速地掌握了它的运作原理。或许除他之外,再没有任何人能以这么快的速度完成这样的壮举。
他将他的思想、他的意志和他的愿望传送到蛇人的头脑之中。几乎就在一瞬之间,暴民中比较顺从的那些便已从高台上离开,走到边上去了。有几个反抗或犹豫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一个接一个照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