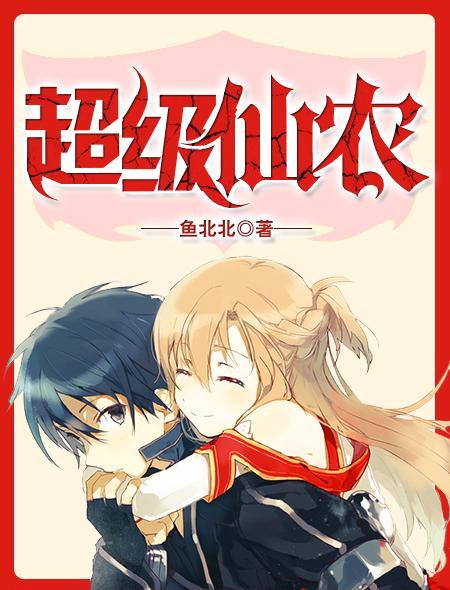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被遗忘的士兵pdf > 第35章(第1页)
第35章(第1页)
那个家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的。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讲述历史。而我们这些失败者,则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懦夫和下等人。失败者的回忆、恐惧和情感是不该被铭记的。
我们第一个夜晚的撤退被随后到来的降雨弄得更加艰难。恩斯特和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让卡车能够跟在坦克后面。如果没有坦克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俄罗斯春天泥泞的道路中开出来。我们不时狠狠地踩着卡车的油门,感到卡车随时都有可能散架。坦克的履带已经将道路变成了很深的泥沼,随后到来的雨水又将这些泥沼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泥潭。卡车的挡风玻璃完全被泥浆所盖住了。恩斯特出去试图把挡风玻璃上的泥浆擦去。
卡车的车灯由于泥浆的遮盖也失去了作用。在夜里我们甚至不能看到前面坦克的位置,尽管坦克离我们只有大约5米远。我们的卡车大多数情况都是与前面的坦克呈斜角状态前进的。我们常常被坦克强行拖回到道路上来。每次这种情况发生时,我都会怀疑我们卡车的4个轮子是否都还在。在卡车后厢的伤员现在都已经不发出声音了‐‐也许他们都死了?
车队继续向前走,天亮时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极度憔悴。在夜里,我们的车队会拉开距离。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是否我们能够准时到达目的地了。我们前面的坦克会突然从道路上向右离开,因为前面的道路甚至连坦克都难以通行了。接着坦克会开上一片灌木丛生的路基,将挡在前面的所有灌木都压到地里。
我们卡车的4个轮子现在都已经成了4个大泥球,尽管卡车引擎还在无力地转动着,但卡车的动力完全需要依靠前面的坦克。然后车队又会突然停了下来。这是我们离开顿河后的第二次中途停车。我们在先前只是在晚上停下来补充燃料。那些坐在坦克后面的倒霉蛋们的屁股一路上都被坦克灼热的引擎&ldo;烘烤&rdo;着,而他们身上其他的部位则浸透在冰冷的雨水里。一场几乎打起来的争吵在一个工兵指挥官和一个坦克车长之间爆发了,其他几乎每一个人都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吃些东西或是去路边拉屎。
这场争执是这样开始的:
一个我们车队军衔最高的工兵军官向大家喊道:&ldo;现在大家休息一个小时!好好整理一下自己!&rdo;接着我们车队里的坦克车长便破口大骂起来:&ldo;去你妈的!&rdo;显然这个坦克车长并不买那个在他看来还很嫩的工兵军官的账。坦克车长说道:&ldo;我们睡够了才走。&rdo;工兵军官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道:&ldo;我们今天早上必须要到别尔戈罗德。显然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军阶。他一边将自己的手放在步枪上,一边接着说道:&ldo;我下命令时我们就出发。这里我的军衔最高,你们必须要服从我的命令。&rdo;坦克车长回复他说:&ldo;如果愿意你就开枪打死我吧,你自己来开坦克。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要走你自己走好了。&rdo;工兵军官的脸变成了绛紫色,他没有再说什么。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我们说:&ldo;你们俩!别呆站在那里,去车厢里看看那些伤员需要什么。&rdo;但那个坦克车长依旧不依不饶,他又说:&ldo;好的,等那些伤员都死了的话,你可以好好地给他们擦擦屁股了。&rdo;工兵军官回答道:&ldo;你等着,我会向上面汇报的。&rdo;现在他的脸已经给气得煞白了。
在车厢里,虽然经过两天几乎不停顿的颠簸,那些伤员并没有死。他们只是不再出声了,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伤员的绷带上被鲜血所浸透了。除了一个双腿被截肢的伤员外,我们气喘吁吁地把所有的伤员放好位置。他们所有人都向我们要水喝。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让他们尽情喝了许多水和白兰地。我们本来不该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人很快就失血过多死了。
我们把他们掩埋在路边的泥里,并在他们的掩埋地上放上木棍和他们的钢盔。然后恩斯特和我回到了卡车的驾驶室里。我们都想睡一下,但我们两个人都全无睡意,只是在驾驶室里这样斜靠着,谈论着和平时的生活。两个小时后,还是那个坦克车长下令出发,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现在已经是早上9点钟左右的光景了。天色晴朗,阳光灿烂,大片积在树杈间的雪从树上落了下来。
那个坦克车长说道:&ldo;哈!我们的将军在我们睡觉的时候离开我们了。也许他喜欢散散步!&rdo;看起来那个工兵军官真的走了。他一定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搭乘路过我们这里的另一队卡车走了。坦克车长继续嚷道:&ldo;那个狗娘养的家伙现在一定正在写报告呢,如果我再碰到他的话,我一定会开着我的坦克从他身上碾过去,就像对待那些布尔什维克一样。&rdo;
我们费了一些气力才从休息的河岸退回到了路上。我们在两个小时以后才到达了一个我已经不记得名字的村庄。这个村子距离别尔戈罗德有大约8公里远。村庄里到处都是从各个部队来的人员。村子里弯曲的道路两边是一排排的小木屋,这些小木屋低斜的屋顶让我联想起了就像是没有前额的人脑袋。村子里被一群群的士兵和沾满泥浆的装备堵得水泄不通,许多士兵正在寻找自己的连队,这里的道路状况要好了许多。
我们将自己的卡车和坦克分了开来,坐在坦克上的那几个工兵现在转到了我们的卡车上。我正在寻找着我的连队,两个宪兵告诉我说我的连队已经去了哈尔科夫,但他们又接着说他们也不太确信,并让我去位于一辆拖车上的军事调度办公室问。我走到了那个调度办公室,问询信息的士兵们把调度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士兵们问询时的喊声。办公室里只有3个心烦意乱的军官负责。我奋力挤到了这几个军官面前,还没有开口就因为加塞被他们训斥了一顿。我想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也许会把我送上军事法庭的。村子里面的混乱让人无法想象,四处游走的德国士兵们一面咒骂着,一面开着玩笑纷纷拥进那些小木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