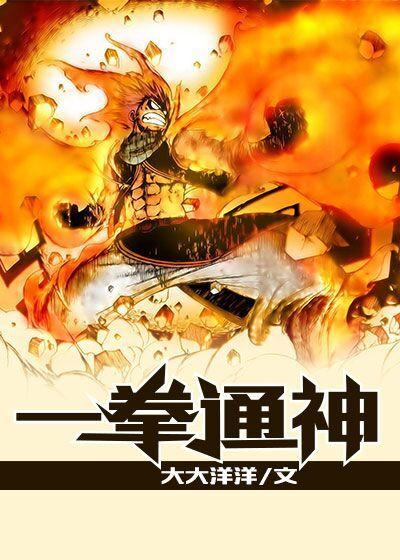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被遗忘的士兵pdf > 第39章(第1页)
第39章(第1页)
&ldo;这里安息着我们的朋友:恩斯特&iddot;纽巴赫&rdo;
为了防止自己再一次的情绪失控,我转身跑回到了卡车上。
一个后面的伤员现在坐到了原来恩斯特的座位上。那个家伙看起来傻呵呵的,一上车就倒头呼呼大睡起来。开了不到10分钟,卡车的发动机便开始抖动起来,接着便熄了火。卡车的抖动唤醒了我旁边这个睡着的伤兵,他问道:&ldo;出什么事了?&rdo;
我回答说:&ldo;没有,只是我们没有汽油了。&rdo;他说道:&ldo;该死,那我们怎么办?&rdo;
我回答说:&ldo;我们只好走路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走走应该不错。轻伤员可以帮助重伤员。&rdo;
我朋友的死让我在顷刻间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我多少为同车的人因为卡车没有油要受些罪而感到有些幸灾乐祸。和我一起的同伴用目光上下看了看我说:&ldo;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走不动路的。我们好多人都还在发着烧。&rdo;
他傻呵呵的自信让我感到愤怒。这个人显然是一个不会问事情究竟的&ldo;二百五&rdo;。在他被派遣到顿河前线后,一发俄国炮弹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几块弹片打到了他的身上。自从那以后,他就一直靠消炎药活着。
我对他说:&ldo;那好啊,你可以待在这里等待救援或是俄国佬,我自己得走了。&rdo;
我下车跑到后门,用脚踢开了后挡板,向大家解释了情况。车厢里面简直臭不可闻。有些人甚至没有听清楚我在说什么。我为自己粗鲁的行为感到害臊。但是现在除了走路外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吗?大约七八个人费力地站了起来,这几个人脸上都已经胡子拉碴,可以看出他们在发着烧。我突然心里感到难受,我不愿意再坚持这些人下车步行。当这几个人爬下车后,他们在议论着车厢里剩下的没法走路的几个伤员该怎么办。
他们说:&ldo;让车上那几个重伤员站起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干脆不要告诉他们,把他们留在这里,也许后面的人会帮助他们的。后面还有部队会赶上来。&rdo;
我们上路了,虽然为那些没法站起来走路的伤员感到难过,但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
我是这里唯一没有受伤的人,也是唯一有枪的人。我把恩斯特的枪给他们,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背。不久后,一个满是泥浆的三轮挎斗摩托车赶上了我们并停了下来,尽管我们没有向他们招手叫停。车上坐着两个装甲部队的士兵,其中一个人慷慨地将自己的座位让了出来,他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下了车和我们一块儿步行。那辆摩托车最后竟然装了3个伤员开走了。
再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了。他文雅的举止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如今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但是还记得我们一路谈论了许多很深的话题。他告诉我苏军的反攻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这片广袤的乌克兰平原上,我们很有可能随时会遇上苏军的装甲部队。我的嗓子开始感到发干,但是我的伙伴看起来对于自己和我们的军队充满了信心。
他说:&ldo;现在春天到了,我们就要反攻了。我们会把俄国佬们重新丢到顿河里去,然后我们会回到伏尔加河。&rdo;
当一个人正处于低谷时,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满怀激情和信心的人真是令人惊讶和振奋。我几乎感到是上天把他送到这里让我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如果恩斯特还活着的话,我会更高兴的。
一直到了晚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农舍。我们小心翼翼地接近着这间农舍。俄国游击队常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和我们一样,他们也需要从农舍中获取休息和食物。
和我一起的那个装甲部队的士兵现在走到了众人的前面,他手里紧握着枪,缓慢而小心地走向那所房子。他在房子背后消失了一会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一些焦虑。但是他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向我们挥手。这个农舍属于一群当地农民,他们细心地照顾我们的伤员们。农舍里的女人们给我们煮了热腾腾的饭食。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痛恨共产主义,他们被从自己在维特布斯克的小农场赶了出来,被迫来到这里的共产主义公社劳动。还告诉我们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屋子借给德国士兵使用。他们这里还有一部水陆两用的大众牌德国军车,这辆军车是由于机械故障被其他德国部队丢弃掉的。他们告诉我们当地的游击队从来没有骚扰过他们,因为这里常常有德国士兵住着。那个和我一起的装甲部队的士兵多少对于农户家里有一辆军用汽车感到不太舒服。这些俄国人也许在撒谎,也许这部车是他们偷的。我们试着发动了一下这辆汽车,发动机能够发动起来,但是车子的传动系统坏了。
那个装甲部队的士兵说:&ldo;我们明天修吧,现在该休息了。我来站第一班岗,你可以在午夜时换我。&rdo;
&ldo;我们要站岗执勤?&rdo;我惊讶地问道。
他回答说:&ldo;我们必须这样。我们不能信任这些人,所有的俄国人都善于撒谎。&rdo;
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晚上要受到焦虑的煎熬了。我走到农舍后面的房间里,那里简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里有一堆麻袋,几捆干的向日葵秆、绳子和木板。我把这些东西拼成了一张粗简的床。当我准备将自己的军靴脱掉时,我们这个同伴阻止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