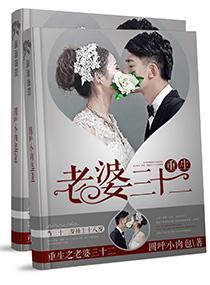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化宋体字 > 第262章 细雨润物(第1页)
第262章 细雨润物(第1页)
淮东之地,这片后世称为江苏的地方正在经历一场大旱。
大宋的救灾制度平稳运行,官府熟练地开仓平抑粮价,但在这场大旱中,大量颗粒无收的佃户带着家小,开始进入城中讨生活。
太子殿下继位来,大作工坊,这些年来,工坊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给了佃户一条新出路,让他们遇到困难时,不用困守在那一亩三分地中,去城中找些最苦的活计,至少也能活下来。
这事带来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那些雇佣佃户的主户们,对佃户们客气了许多,在以前,他们对佃户几乎是掌握着生杀大权——主户若是不愿意佃户们继续租种,那大多数佃户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土地租种,那便是断了生计。
正因此,平时大户的权力是极大的,佃户便是损了利益,也要忍气吞声,而当有了新的出路后,主户们的生活质量便下降得厉害。换以前,他们想找佃户做帮手,只要说一声就行了,现在他们都会推三阻四了。
运河之上的码头上,又是一家老小提着包袱,走上货船。
淮南路夹在汴京、杭州、密州这三个新兴的大城之间,很多人过不下去时,便会外出讨生活。
如今淮海东路的人有三个选择,一个是顺着运河南下杭州,一个是乘海船北上密州,还有一个便是顺着运河去西北边的汴京。
“走吧,”为首的老人轻杵拐棍的,“东京城是天子脚下,工坊最多,船费也不贵,不像南边那么克扣。咱们就去东京城。”
一家人都上了写着“陆”字的货船,而在这支船队中,后方还有一位意气风发的文士,他三十出头,是“淮西提举常平”,管理着淮南西路的常平仓,今年因为救灾有功,加上已经到三年的考评之期,回京述职,眼看又要升官了。
但升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次去京城,不知道能买到多少书,”陆宰感慨着道,“自从油印之道盛行以来,书价日降,对我等爱书之辈,实是盛事。”
他的妻子唐氏闻言笑道:“你与父亲一般爱书,这些年图谋我家藏书还嫌不足,如今要去谋那京中书院了么?”
陆宰大笑道:“夫人知我!”
夫妻二人同乘一船,看着两岸青山小镇退去,颇有些山水之趣,唐氏突然道:“听闻北方要疏浚御河,让燕京的大石碳船可以过汴京直入杭州,此事可真?”
陆宰摇头道:“只是疏浚黄河到东京城这一小段,河工耗时费力,听说朝廷还在召人勘查地形水势,要我看,燕京之船可以过东海而至杭州,不必劳民伤财,这南边的河道关系天下,才更该疏浚。如今朝廷为此争论不休,要我看,还有的吵。”
“自太子解封海榷以来,蜀地、京城的船越发多了,汴河时常有舟船阻塞,”唐氏也是大家出身,揶揄道,“是如今淮南路想要运河,做些补益吧?”
陆宰断然否认:“哪有,朝廷不许在汴河上重复设卡,淮南路的知州又想要些政绩,自然要想些法子。”
说到这,他又感慨道:“如今大家是看出来了,当今太子是个管事的,有什么需要,只要理由足够,他便会想办法,哪怕没办法,被安慰一番,也是在太子面前露了脸。”
唐氏也道:“不错,这几年来,天下可真是安稳太平,江南之地元气渐复,有他真是大宋之喜啊。”
这时,她看见旁边的货船那狭窄的尾舱上正挤着一家人,一名朴素女子正在船尾织着毛线,一个小孩正在她腿边叫着姐姐快和我玩,不由惊讶道:“那是哪家佃户,怎么不去客船,要搭尾舱?”
“那是宜兴一家姓李的佃户,家中受灾,咱们尾舱未满,便随意载了多搭了一家人,”陆宰随意笑道,“咱家那位船头,看到货仓没满,便会急着团团转,改不了了。”
唐氏也笑了,看了一会小孩,忍不住摸了摸肚腹:“也不知那京城的太医,能不能治治我这胎腹。”
“别想太多,”陆宰拥住她,“你这些年吃得苦头不少了,我陆家子嗣丰足,大不了过继一子。”
唐氏摇头道:“那怎行,官人对我情深,我必得让陆家有子嗣继承才好,我不但要有孩儿,将来还得给咱们生十个八个孙儿!”
陆宰无奈抱住妻子,又是一番安慰。
……
船队紧赶慢赶,在河水浮冰断航前来到了京城。
繁华的城池威严高耸,城外也早已是大片住宅,城东已经围绕着神霄院、新军军营、附属工坊形成了比城内还繁华的商业中心,而城南则以泽园为中心,形成了巨大的消费群。
两处中心有效地疏解了主城中拥挤的人流,缓解生活压力,让整个城市有更大的活力。
周围的城镇道路四通八达,许多村中鸡蛋蔬菜都能很快运到这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形成
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中心,而这个中心又像一个黑洞,吸纳着周围的粮食、人口。
唐氏与陆宰离开船,去了自家在京城的宅地,略做歇息,就开始与亲友相互拜访。
唐氏发现,京城的各家女儿们如今开口闭口,都在谈治家治国,聊插花、点茶、书画女工的基本才能没有了,一时居然在各家闲聊中挤不进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