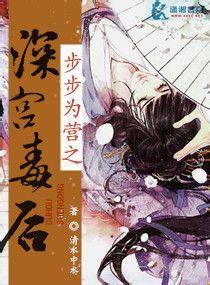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落鸢女主叫什么 > 第一百二十七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第1页)
第一百二十七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第1页)
一个月前。
再去南昭的前一个晚上,拓跋傲扬自落鸢阁回来,却见了胡顺子急匆匆进来,还未来得及问只见胡顺子“砰”的一声跪倒在地,面上有一丝僵硬。
“何事?朕不是叫你去准备明日去南昭的事宜吗?”
“王上……王上派奴才查的事情,奴才派人去寻了前朝六老,却发现几人同时患疾猝死,奴才只查得一条线索,”所问,且声音越来越弱:
“那面具人与颜瞿并关联,反而是王上您,与南昭将军颜瞿有莫大的关联。”胡顺子答道
“继续说。”拓跋傲扬厉声道。
“奴才不知。”胡顺子头低得已经磕到了地上,整个帐内安静得只听见呼吸的声音,拓跋傲扬手腕一斜,碰掉了放在桌案上的青花盖碗,在地上摔得粉碎。
拓跋傲扬猛地起身道:
“备马!连夜去玉台山,不准惊动任何人!”
只有去见他,一切谜底才能揭晓。
一场春雨突如其来,有拈花般轻柔地姿态,轻抚着万物,却在一瞬间骤急比。
马匹穿越了山间的丛林,才与黑暗中的一方屋宇前停下,胡顺子接下拓跋傲扬滴着雨水的黑色斗笠,跪下身为他拭干被雨水溅湿的衣摆,拓跋傲扬一脚蹬开他,将衣袍一扬便就地跪下,胡顺子诺诺地不敢言,赶紧俯身低头跪在他身后。
细密的雨水自拓跋傲扬的额间滑过,在坚毅的眉峰上凝结成小粒的水珠,他却一动不动地跪着,连要擦拭的意思都没有。
不一会儿,屋宇的门终于开了,出来一个身着粗布的老者俯身对拓跋傲扬道:
“王上,老主人请您进屋。”
拓跋傲扬抬眼看了看来人,眼中闪过一丝惊异,又在一瞬间受了目光依礼含额道:
“多谢。”便起身进了屋。
屋中陈设甚是简陋,眼前的老者阖目养身,桌案前放着书卷,和一盏紫砂茶壶具,烛台跳跃的光映得他脸上显出安详的神态。
“父王。”拓跋傲扬上前一步,跪在了老者的面前。
他便是北朔的先皇,自拓跋傲扬登基后隐于玉台山。
“扬儿,为父以为此生不予相见了。”老者看着来人,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前朝六老死了。”拓跋傲扬低声道,他要的是一个解释,一个他父王给他的解释。
“有些事情知晓了,反而是不妥,扬儿为何执意而行。”老者边说边动了动手腕,合上了面前的书卷。
“但是儿子必须知晓,儿子与颜瞿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何在儿子调查此事的时候知情的前朝大臣都不约而同的死去,为什么整个硕大的北朔皇宫没有一个人知晓当年的拓跋傲扬身在何处?”
老者轻声一叹,眼中存着一样的情思道:
“既然扬儿已经猜得到原因,又何必再来问为父?”拓跋傲扬的眸子一下子变得灰暗比,良久才缓缓道:
“我就是从小被送自南昭皇宫的颜瞿?想必那是父王创造的一个假身世假名字,如此才让我被南昭皇帝所信任,让我成为立下赫赫战功的南昭大将军。而我的存在为的就是将来的一天能与北朔里应外合,一举倒翻南昭京都?而父王你千算万算却算不到因为一些变故我被派往了边塞镇守,于是你们捉住这样阴差阳错的机遇,将错就错让我从回到北朔,并消除了我一切关于颜瞿的记忆,而模样也因药的副作用而有了改变。”拓跋傲扬顿了顿嘴角微微扬起自嘲道:
“呵,从始至终,儿子就是父王您反攻南昭的一枚棋子!”
老者听着拓跋傲扬的话,佝偻的身子微微一颤道:
“为父知道这一天终究会来,你也终究会知道。可是,扬儿,你想错了,若是为父心要你继承大统,为父就不会如此煞费苦心了。当年杰儿被俘,落下了再也法成长的恶疾,你若留在北朔皇宫长大,南昭皇帝怎么能容得下你?为父索性与六位重臣计划了此自入虎穴的计策,为的就是你能健康的成长,将来能独当一面,重振我北朔的国土!”
“可是父王,儿子也是人,并非冷血之物。您让我攻打的是从小养育我的土地;您让我杀的是自小和我为伴的兄弟;您让我忘记的,是儿子生命中最快乐和忧虑的日子!父王您于心何忍?于心何忍…”拓跋傲扬低吼道,男儿何于此地?风月过境,何为亲情?何为忠义?到头来是一场幻梦,若是白活了整整二十年也罢,却连那二十年的日子也亦如白纸。
老者微微摇了摇头,布满皱纹的脸上突然呈青筋暴突状,一口黑血喷出,在卷轴上溅开一朵血花,骤然向后倒去。
“父王!”拓跋傲扬心里一惊,猛然扑过去,伸手一摸,已经没了气息。
他身子一震,心里明白了过来,方才他进来时,父王便已经服下慢性毒药了。他神色渐然痛楚,突然放声大笑几声,那笑声凄凉而阴冷,尽是伤痛之情,如此笑了良久,全身似被抽干了力气一般才神色颓然靠于桌腿边。
二十年的记忆余生的伤痛他以他年迈生命的终结统统还予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