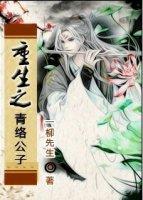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鲁伯特差分机 > 第153章(第1页)
第153章(第1页)
侍者走开以后,韦克菲尔德大声叹了一口气:&ldo;真该死,奥利芬特!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rdo;
&ldo;安德鲁,你到底在害怕些什么?&rdo;
&ldo;这不是很明显吗?&rdo;
&ldo;有那么明显?&rdo;
&ldo;加尔顿勋爵已经跟你们那个该死的埃格蒙特结成了同盟,而他是刑事人体测量学部门的大靠山,他一直都是,那个部门简直是他建立的。他还是查尔斯&iddot;达尔文的堂兄弟,在贵族院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rdo;
&ldo;是的,他在皇家科学会也有影响,在皇家地理学会也一样。我对加尔顿爵士非常了解,安德鲁,他主张对整个人类推行系统化繁殖。&rdo;韦克菲尔德放下刀叉。&ldo;刑事人体测量学部门已经实际控制了整个统计局。现在统计局上上下下,已经完全被埃格蒙特控制。&rdo;
奥利芬特凝视着他,发现韦克菲尔德的上齿又开始咬下唇。
&ldo;我刚从福利特街赶来,我们这个社会的暴力冲突,&rdo;奥利芬特从衣兜里取出那把巴利斯特-莫里纳左轮枪,&ldo;或者我应该说,不被承认的暴力泛滥程度,已经非常惊人。你不觉得吗,安德鲁?&rdo;他把左轮枪放在两人之间的铺着亚麻布的桌面上,&ldo;就以这把枪为例。有人告诉我说,这种枪非常容易得到。这是法属墨西哥地区的产品,尽管设计者是西班牙人。我还听说,枪里面的某些部件,比如弹簧之类,实际上是英国制造,在公开市场都可以买到。这样一来,也就很难判断这样一种武器到底来自哪里。这很好地象征了我们目前面临的局面,你不觉得吗?&rdo;
韦克菲尔德脸色煞白。
&ldo;看来我是吓到您了,安德鲁,我很抱歉。&rdo;
&ldo;他们会除掉我们的,&rdo;韦克菲尔德说,&ldo;我们两个都会从此消失。什么都留不下,甚至没有人和东西证明我们两个存在过。后人找不到哪怕一张购物小票、一笔抵押贷款,什么都找不到。&rdo;
&ldo;我要做的,就是为了要制止这些发生,安德鲁。&rdo;
&ldo;你少跟我装清高,先生,&rdo;韦克菲尔德说,&ldo;还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开的头,奥利芬特‐‐让人失踪,让文件丢失,删掉姓名,除去编号,为了你们特定的目的篡改历史……不,你没资格对我说教。&rdo;
奥利芬特无话可说。他站起来,那把枪就留在了桌面上,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烤肉厅。
在大理石前厅,有一位穿着紫色制服的职员正在从铺着细沙的大理石烟灰缸里面向外拣雪茄烟头。奥利芬特问他:&ldo;请问一下,能否麻烦您带我去找俱乐部的管事?&rdo;
&ldo;找我就对了。&rdo;职员好像是说了这么一句美国口头禅,然后就带着奥利芬特静悄悄地离开。两人经过一段走廊,两边都是镜子和塑料植物。
五十五分钟之后,奥利芬特已经粗略浏览了兰姆之家的各类设施,看了一份画册,上面有每年举办的各种&ldo;余兴演出&rdo;。为此他申请了俱乐部会员身份,用自己的国家信用账号付了一笔数目可观且不可退还的预付费。奥利芬特与油头粉面的管事握手话别,给了他一英镑的小费,要求从俱乐部最偏僻的员工通道离开。
这条通道连接着碗碟洗涤室,出去之后,正是他想要的又黑又窄的街道。
一刻钟以后,他已经站在拜福德路一间繁华商厦的酒吧里,再次阅读一个叫西比尔&iddot;杰拉德的人发给贝尔格拉维亚的国会议员查尔斯&iddot;埃格蒙特的电报。
&ldo;老爷,我的两个孩子啊,全都病死在了克里米亚,他们就给我发了份电报,告诉我他们都没了‐‐你那儿也是那样的电报吗?&rdo;
奥利芬特把那份电报折起来,放回烟盒。他凝望自己倒映在酒吧白铁皮墙面上的影子,看看空空的酒杯,又抬头看看那个走过来搭讪的女人:她年事已高,头发蓬乱,满身的破衣烂衫,颜色已经无法辨认,灰扑扑的脸颊笼罩着驱之不去的愁云,因为饮酒,两腮微有些泛红。
&ldo;不,&rdo;奥利芬特说,&ldo;我没有遇到过那样的悲剧。&rdo;
&ldo;我还以为是呢,&rdo;她说,&ldo;我的汤米就是那么没的。一丝布条儿都没送回来‐‐好好一个孩子,连丝布条儿都没剩……&rdo;
他给了那老婆婆一枚硬币。老人向他道谢,然后嘟嚷着走开了。
看来他总算暂时甩开了跟踪者。他现在完全是孤身一人,该去找辆出租马车了。
在幽暗、高大的火车站内,上千人的话语声似乎揉合到了一起,原本语法正常的语言被钝化成了迷雾一样的听觉体验,无法辨认,也无法穿透。
奥利芬特井然有序地忙碌着他的事务:他先是买了一张去多佛尔的头等铁路车票,预定乘坐晚十点发车的特快列车。售票员把他的国民信用卡放在订票机器里,用力扭动摇杆。
&ldo;好了,先生。已经预定在您的名下。&rdo;
奥利芬特谢过售票员,又溜达到另外一个售票口,再一次出示信用卡后说:&ldo;我想预定明早去奥斯登的船上包间。&rdo;随后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在收起船票和信用卡之前,他要求再买一张午夜前往加莱的二等舱船票。
&ldo;您是要今晚的票吗,先生?&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