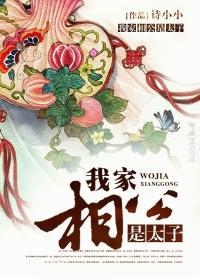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后宫不受宠的日常 百度 > 第75章(第2页)
第75章(第2页)
“我想让主子活久些,我死在主子前头。可一想到我死了,没人照顾主子,实在放心不下,我就想哭。可若是比主子晚走,主子走了,我连祭文都无法为主子写,想主子了,该怎么让主子知道?”
他哭得很痛。
贺玉听了,惊讶片刻,轻轻道:“珠玑,我来教你写。”
珠玑只是识字,却不会写字。
“这不难。”贺玉说,“从现在学,十年,二十年,一篇祭文,总是能写成的。”
他开始教珠玑写字,自己闲下来时,就会把还记得的一些事,记录在纸上,一点点整理好,收起来。
贺玉教了珠玑十三年,总归是珠玑离他先去。
珠玑离开后,他开始专心整理书籍,记录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有许许多多旧人在他之前离开。
永安十九年,皇帝送了他一副琉璃镜,是宋廉用过的。
楼英也不怎么爱说话了,一天内的多半时间,都是在摇椅上哼曲渡过。
永安二十一年,六皇女赵盈病逝,那年,昭王府年年盛开的桃花,罕见的未开一朵。
永安二十三年,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到昭王府拜会贺玉,她从包裹里拿出了还未成书的游记和舆图。
“这是我母亲留下的。”她说,“我母亲生前所著,有一本《西南山河异志》,听闻齐王殿下一直在找这本书的手稿,我亲来送上。”
她的女儿入了这次春闱的一甲,在吏部任职后,接她上京,她就把书稿也带上了。
那晚,贺玉把手稿拿给楼英看,两个人一页一页翻着。
“这是我家,没错,就在这座山下,就在这里。”
贺玉听楼英激动地讲着,讲他儿时的往事,讲他的姐姐,他的家。
永安二十三年,楼英离世。
皇帝以军礼厚葬了他,他身披铠甲,握着未开刃的刀,还有一本《西南山河异志》,葬在了帝陵。
昭王府,只剩下贺玉一人。
往后十年里,他送走了妹妹,送走了几个黑发人,接到了西北发来的有关文宝的讣告。
王府的树郁郁葱葱,他常坐在树下,脊背挺直,身形几十年如一日,清瘦如松,端坐着,拿着一支笔,推一推鼻梁上的琉璃镜,一点点写着他的回忆。
到了夜晚,就将他们收进匣子,放好。
他卯时起,酉时息。
清粥小菜,无悲无喜。
他看起来,并没有那般苍老,神情仿佛从未变过,像一棵活着的树,安静又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