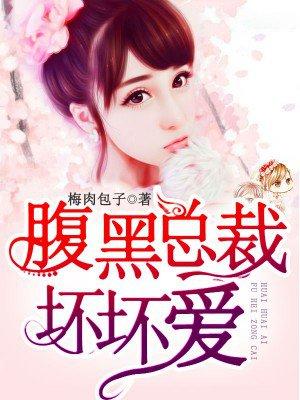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二嫁全文 > 第16章 父子间的悄悄话(第2页)
第16章 父子间的悄悄话(第2页)
“所以您才在慌乱之中选了蒲州邵氏?”
老侯爷没有正面作答,叹了口气,颇有遗憾的说道:“只可惜啊,老大他还不懂。”
谢时郢接过话:“大哥可能是有自己的考量吧,他在军中颇有建树,也深得靠山王信重,我只是想,这次的事,应该不会和翟辛结怨吧。”
“要结怨,早就结了,你二叔这次的事何尝不是他翟辛的手笔?他想在朝廷三司处安排自己的亲信党羽,老二正好挡了他的道!我们谢家这些年在京中避其锋芒,让你二叔去避一避也是好事,省得他那个炮仗脾气指不定惹出什么事?”
谢时郢敏锐捕捉到其中的关键信息,问道:“二叔此次判决下来了?”
老侯爷摇摇头:“尚未,想必陛下看在我与他年少伴读的情谊,这事也不会让翟辛做得太过分的,为父猜测,估计是贬职外放吧!”
老侯爷把话题转回来:“这邵氏女,我看就挺好,只要不薄待了她去,日后不论是你大哥还是你,想要在这乱世中有一番建树,光耀我谢家门楣,江南应该会提供不少助力。邵氏兄长那边我已去信拜托了益州的建司知州照拂一二,他与我有同窗之谊,应该不会置之不理。假以时日,江南地区作为你们兄弟二人的大后方,有钱有粮有人,也就不枉我这一番筹谋了。我时日无多了,侯府就靠你们兄弟两了。”
谢时郢听闻,一个跨步上前,握住老侯爷的手:“阿爹,你胡说些什么?”
老侯爷笑笑,并不言语。他自己身体什么样他太清楚了。
过了一会儿,挥手让谢时郢和廖管事退下,他准备喝药休息了。
二人恭恭敬敬退出居所。
屋外,谢时郢叫住廖管事。
廖管事行了礼:“二公子可有事?”
谢时郢目光审视着廖管事,并不说话,廖管事被看得有些忐忑:“老奴这是脸上有字?”
谢时郢扯扯嘴角:“廖管事你在侯府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吧,对父亲和侯府忠心不二,时郢十分感动。”
廖管事闻之,面容羞赧:“二公子哪儿的话,老奴是侯府的人,自小便跟着侯爷,对侯爷吩咐的事肝脑涂地,绝无二心。”
“哦?”谢时郢眉头一扬。
“那你怎么没将昨日你在筠园拿金豆子这事禀告给侯爷?”
廖管事一愣,面如土色,忙解释道:“老奴一时利欲熏心。。。。。。”
谢时郢却堵住了他后半句话,表情变得和煦起来:“廖管事别紧张,我只是随口一问。”
廖管事呆愣愣的没反应过来,谢时郢笑道:“我自然知道那是大奶奶赏的,只是侯爷刚刚问你的时候,让你一五一十秉明了说,你却没提这事,我以为你忘了,给你提个醒而已。”
初春的夜里还不至于太冷,但廖管事的后背已经起了一层细小鸡皮,他在侯府三十多年,早已知晓大公子性情冷淡不善言语,三小姐刁蛮任性,只是这二公子,平时温和谦逊,但私下里确实颇有城府,心思难辨。
谢时郢见敲打廖管事的目的已经达到,也不耐烦再吓唬他,挥了挥手,让他下去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筠园的方向,神色淡淡的,内心腹诽:“不愧是江南富户,一把金豆子,她倒说赏就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