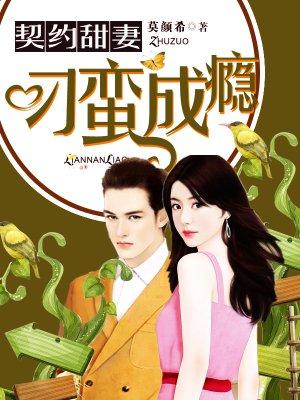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吾妹多情全文免费阅读 > 第129页(第1页)
第129页(第1页)
越绣越灰心,心里有过无数个念头想要作罢,可一想到绣得难看也是好事,横竖哥哥也不会佩戴出去。她绣的东西,不过逗人一笑罢了。三日之后,这只长颈兽香囊落到了谢昶手中。他看着这麒麟兽通天长的脖子,再加四只小短腿,沉默了足足片刻。阿朝在一旁闷声用膳,见他一直在瞧,不禁有些羞怒,伸手便要夺来:“不喜欢还我,我送给旁人去!”谢昶却抬手一让,攥紧手中的香囊,轻笑一声:“哦,你想送给谁?”她不知哪根筋不对,张口便道:“太子殿下不是让我给他绣只香囊吗?他倒是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我悄悄给他,不叫太后知道。”说完这句立马后悔了,她有些心虚地错开男人瞬间冰冷沉戾的眸光,默不作声地扒碗里的饭菜,却有些食不下咽了。屋内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僵持,她不敢抬头瞧他,怕他误会自己对太子心存念想,又气自己蠢笨,胡乱说话惹他不高兴。静下心来想想,方才一时冲动脱口而出,其实也有动机,似乎就是想说些不好听的气气他,好让他把自己放在心上。可越是这样想,就觉得自己像个孩子,脾气莫名其妙地上来,满身的荆棘对着自己最亲的人。翌日,尚书房。谢阁老今日似乎心情不大好,眉眼肃然,一双凤眸沉得厉害,通身的凛冽之气,教训起人来丝毫不留情面,整个尚书房无不屏息凝神,谁也不敢窃窃私语。太子战战兢兢写完课业,眸光微微一抬,那道绯红鹤补在眼前放大数倍,眼里却在同时撞进个诡异的东西。悬挂在他腰间的那一枚……小怪兽香囊。冷郁的男人气息中和了滑稽的香囊带来的不适配感,也沉沉地压在他笑穴上,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当面嘲笑谢阁老的香囊啊!“太子殿下在看什么?”头顶传来一道冷冽的嗓音。“没……什么。”太子头埋低,双手递上自己的策论,果然又被冷冷数落一通。课后太子同陆修文说起那枚香囊,陆修文却沉默片刻,只勾了下唇角:“殿下觉得那香囊会是谁绣的?”太子一愣,这绣工不会就是阿朝妹妹吧?一想到出自她手,那奇奇怪怪的纹样似乎都变得可爱了起来,可欢喜过后,太子心里只剩一片空空荡荡。再可爱的姑娘,终究不会是他的了。绿树阴浓夏日长。树上的青杏累累如珠,阿朝每每下学路过都不禁感慨,这若是等杏子全部成熟,阖府上下都分上一遍,也未必吃得完。她伸手去够一处结满果实的低枝,想摘几个下来做青杏糖水解解馋,崖香便在一旁掀起围裙兜着,给姑娘放果子。这一枝不算高,阿朝踮踮脚摘了几个下来,再要多些就只能跳起来摘了。夏日衣衫轻薄,手臂抬起,宽松的衣袖直褪至臂弯,夕阳的余晖穿透青碧的枝叶,落在少女明晃晃的细白藕臂,细腻得凝脂一般。谢昶又想起幼时那个喜欢爬树摘果子的小丫头,她还真是一刻都不消停。阿朝又勉强摘了几个,再跳起来便有些吃力了,初夏的暑气蒸得她面颊微微泛了红停下来喘口气,再要去摘,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从后伸了过来。男人身材高大,轻而易举便将那截枝桠压低,满满当当的果子骤然撞入眼眸。她一怔,随即抿抿唇,轻松地摘下几个,“哥哥,你怎么来了?”昨晚闹得不欢而散,原以为他今日不会来了。他还是一身绯色官袍,想来从衙署下值就直接过来了,阿朝将摘完的果子放在崖香的围裙里,眸光一扫,才瞧见他腰间玉带上悬挂的香囊,霎时瞳孔一震。竟……竟然是她那只傻呆呆的长颈兽!阿朝盯着那东西,半晌才喃喃开口:“你不会是将这东西戴出去一整日吧?”谢昶漫不经心地垂眸看一眼,又撩起眼皮,凉声道:“是又如何?”还“是又如何”!大哥,您可是当朝首辅!佩戴这个合适吗!阿朝声音里都带了哭腔:“你不怕人家笑话你?”谢昶嘴角勾了勾:“谁敢?”阿朝欲哭无泪:“虽然……但是……这只是我随手绣着玩的,根本没想让你戴出去呀。”谢昶冷冷一笑:“太子戴得,我戴不得?”◇◎男人的温热气息覆上来◎阿朝将摘来的青杏用盐水清洗干净,一部分腌在瓦罐内做糖渍青杏,另取几枚撕去表皮,倒入冰糖水中熬煮。晚膳过后,阿朝给他舀了一碗煮好的糖水,谢昶不太吃甜,浅浅抿了一口,眉头直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