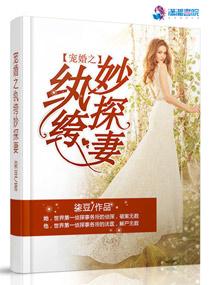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命定终笙txt资源 > 第九十八章(第2页)
第九十八章(第2页)
我开始酗酒,工作也不再上心,领导找我谈过几次话,我也是左耳进右耳出,他们无奈,我也无法。
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两星期,才出月子的叶法医来找我。生了宝宝的她倒没见胖,精神也超级好,一见面她卷起手里的书对着我的头一阵猛敲:“夏图死了吗?夏图死了吗?夏图死了吗?没死你摆这副颓废样给谁看,是男人的就去想办法叫醒你女人?别告诉我你不喜欢夏图?别否认,我最讨厌有话憋在肚子里不说的人。敢否认?敢否认我削你!”
我苦笑:“可是大夫都说她不会醒了,就算我想说我喜欢她,她也听不到了。”
“医生只是说98%的可能,那不是还有2%呢吗。你没听过一句话吗?真发生在世界上的往往都是小概率事件,真理总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叶医生挥着拳头像在喊口号,可不知怎么的,我突然看到了希望。
是啊,还有2%呢。
我查了许多资料,对像夏图这种患者来说,和她说话似乎能唤起她的意识。我是个粗人,不大会说故事,可是还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上了。
“从前,在一座森林的古堡里,住着一个睡美人,她的头发是金色的……”我的第一个故事才开头就被叶南笙一巴掌挥断了。
“夏图就算是睡美人,那你也是个假冒伪劣的王子,不然你亲她,看她醒不醒?”
我的第一个故事在叶南笙的嘲笑声里告终。
第二天,队里有行动,是起失踪人口案,头儿犹豫着要不要我去。我说,我去。
因为夏图不会喜欢窝囊的男人。
案子有些波折,前后告破花了半个月时间,回来后我和夏图说那起案子,我发现我还是擅长说这类的故事,后来叶医生又来看夏图,听到我和她说这个,没揍我。
我偶尔还和夏图说起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淘气,有次爬墙把腿摔断了,在家里养了一个月,那时候我妈不让我出门。
“夏图,我才躺了一个月就腻歪死了,你那么爱玩,怎么有这耐性躺这么久,快起来吧。”那天我趴在夏图的病床前睡着了,梦里我恍惚觉得有人拿手轻抚我的脸。
再后来,等我把我小时候的事情都说完了,我开始说起我和夏图:“你都不知道,你才来队里的时候毛毛躁躁的,光毛躁也就算了,还特爱说话,每天叽叽喳喳的,我都快烦死你了。可谁允许你随便钻进我心里的呢?夏图,你再不醒我可要揍你屁股了,夏图……”
我眨眨眼,发现了什么。
那天,是周末,我下班后去看夏图,才说了一会儿话就接到了主任的电话。
“主任,我还挺年轻的,暂时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房间很静,只有氧气机的泡泡声,手机没开在免提,不过主任的大嗓门还是很清晰:“小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不过夏图那丫头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你不光要为你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父母考虑,我这个侄女人漂亮,年纪和你也想仿,我的意思是要不你们先接触接触?”
“这……”
我还没这个明白,手机就被床上的人夺了过去,前一秒还闭着眼的夏图对着手机话筒吼:“主任,挡人姻缘很缺德,这个姓戴的是我的!我的!”
不装了?夏小姐?我朝她伸过手去……打屁股。
番外三:
我叫龚克,我太太叶南笙习惯叫我902,那是我在临水住宅的门牌号,不过现在901和902已经是没区分的了,因为两户之间早被我打通了一扇门。
清晨,叶南笙的宠物,一只名叫龙龙的美国鬣蜥总是偷偷摸摸从阳台往叶南笙原来的住处爬,每当这时我就知道,指不定是我那盆稀有植物又遭殃了。
我不是没和叶南笙抗议过,可龚太太总是老神常在的反问我一句:“902,你爱我不?爱我还不舍得拿几盆花喂我们龙龙啊?”
舍得是舍得,可是照着龙龙越来越叼的口味看,我是不是该考虑种点向日葵之类的算了呢。
在我冥思苦想时候,我六岁的儿子从婴儿房慢悠悠走出来:“爸爸,妹妹又哭了。”
忘了说,我和南笙婚后第六年,我的二女儿出世了。从长相上看,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长得都像南笙多些,同事们每次拿这事儿打趣,我都无所谓。孩子长得像龚太太没什么不好,她比我好看。
可有件事我却郁闷了,那是我和叶南笙婚后的许多年,我在B省省公安厅刑侦科做犯罪心理的技术指导,龚太太也离开了学校,她在法检科任主任,我们在同一栋大楼工作,每天一起乘车上班,下班时再手挽着手一起走出楼宇。做了我多年上司的许老总是取笑说我们模范地让省厅上下都嫉妒,这没什么不好。
婚后的第一次分歧是在疼疼高中毕业报考那年,几乎是和当年岳父一样的经历,龚太太以谁输了谁说了算的耍赖理由让我的大女儿选报了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的法医学专业。
决定下来,我情绪闷闷的,我抬起头看眼龚太太:“看起来将来再决定儿子和囡囡专业的时候我也要输下了。”
龚太太却连连摇头:“No,no,no,到时候的规矩就是‘谁是女人谁说了算’了。”
我:……
后来,我和岳父说起这事,岳父悄悄和我言传身教:“其实你妈和我闺女都是一类人,不是孩子自己愿意,他们也是不会勉强的。”
我心领神会,自此每晚给儿子女儿的床头故事,内容自动从白雪公主变到了消失的肋骨。”
儿时的熏陶相当重要,可我怎么觉得女儿看我的眼神泪汪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