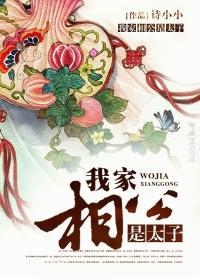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无色txt > 第55页(第1页)
第55页(第1页)
钟情木着脸,不回话,黑发里的耳根却红了。像是要烧起来。周思游再优哉游哉添了把火,“幸好昨天咬的是我。不然小钟导会不会就地自戕啊。”“……”钟情更不出声了。大概在艰难地消化着事实。周思游忽而又道:“小钟导,我没听错的话,你刚刚叫了我一声‘周佳念’吧?我可不可以大胆猜测,你对我的生气,不仅是出于一个导演对演员不敬业表现的生气,也是因为……”“小钟导以为,我变成了酒后随便和人开房的坏女人,所以感到生气?”她话音落下,钟情猛然错开身,背对周思游,不再看她。偌大的影棚里,静可闻针。声控灯有一下没一下地跳动着。钟情面前平板息屏,电脑上的屏保慢吞吞地走着程序。两个人敌不动我不动,僵直得像两尊雕像。“……对不起。”片刻后,是钟情再次开口。她瞧向周思游,认认真真向她道了歉。“我……我不该不明原因就发脾气,不该在手机上无视你的消息,不该不听你解释,也不该强行……在你身上,咬、咬……咬……”她垂着眼,断断续续重复那个“咬”字,耳朵红得滴血,瞧上去羞愤欲死。周思游适时打断她。“好啦,小钟导,知道你是气在头上。”她慷慨大方地说,“我接受你的道歉。不过,最后一个……”周思游靠在沙发椅上,歪歪斜斜着身子,懒洋洋地笑。“其实也没什么关系。”“我不介意小钟导多咬几次的。”作者有话说:钟情:真有能耐啊,昨天去开房了?小游:没有开房啊,就是在车里(无辜)钟情(掐人中)你去死吧!!周思游话音落下,钟情腾一下,站起身,小幅度踢了她一脚。“好好演戏,别现眼。”面色依旧冷淡,语气却捎了笑。周思游故作委屈:“我没戏演了,小钟导把我戏份踩光了。”“那就……好好工作。”钟情改口,又小声解释,“上个月教母的演员就向导演组申请戏份推前,希望赶在春天到来前结束。青川湖这片山冬天荒芜,初春却山花烂漫,她说她的鼻炎撑不到那个时候。”周思游‘哦’了下。“你把我推后,成全她。”“本来只想排班紧凑,没想把你推后。”钟情说,“但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现在季明欣看到你就想笑。她的共情力很强,演戏靠代入体验,但演技并不是很好;如果总是游神……就更无法到达及格线了。”钟情明明在认真道歉又认真解释,周思游却皱着脸,故意问她:“真的不是因为和我的私人恩怨,所以公报私仇吗?”哪想钟情坦然说:“有一点这个成分。本来你作为第一主角,在我这里有优先级,但早上那个误会之后,优先级没有了。”“……”周思游问她:“那现在误会解除了,我的优先级还在吗?”钟情错开视线。大概是晚餐时间过半,影棚外渐渐有人声聚集。钟情听见响动,抬手关了电脑,转身瞥一眼周思游,回她:“看你表现。”或许真是临近冬末,冰雪消融,次日的教堂日光绚烂,一副雪后逢春的模样。周思游站在片场,身后是一人“阿嚏、阿嚏”的声音。是教母的演员。周思游与她对视一眼,便见对方面上挂起一个无奈的笑。明天是教母最后一场戏。但此刻她瞧着周思游,却扯一扯嘴角,捏着鼻子,满脸都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的悲怆。周思游也向她笑一笑。周思游和教母对场并不多,唯一的高光对手戏是冬日的教堂,她们作为两个全然陌生的人,并排坐在花窗外的长椅。姜近的手里是一册书籍,教母手中则是一个小小的头绳。是她已故去的女儿的头绳。教母领养的小女孩成为了神父不法聚财牟利的牺牲品——这是教母对神父怨怼的缘由。神父在世俗规定上罪不至死,教母却不想这么放过他。自小沐浴在圣经下的人,也在那一刻无视主的教导,想要犯戒。这是人性的憎怨欲。姜近问教母头绳的故事,教母闪烁其词。毕竟只是陌生人。眼见气氛沉默,教母礼尚往来,把视线掷去姜近膝上的书,询问:“那……你读的是什么书?”姜近回答:“一本很痛苦的书。”痛苦……的书?教母不解。好奇心驱使下,教母拿起长椅上剥下的书封,细细读出书籍腰封上的简介。这大概是一本回忆录,一个女孩写下自己的故事。童年遭遇侵犯,家长不作为,世俗劝她嫁给强·奸犯。她在这样痛苦的世界里反复解离,用药物持续生命,写下这本书后,最终精神崩溃,至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