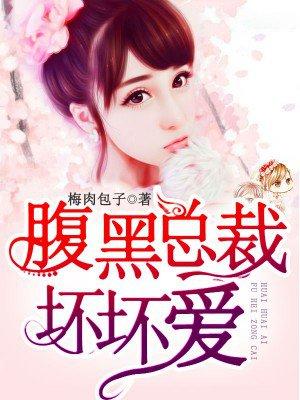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将军全文阅读 > 第五十九章(第1页)
第五十九章(第1页)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子喜欢男的,跟我费什么话。大晚上来找你,自然有十万火急的事,我问你,勿黎的军队要是抓了战俘怎么处置?会不会下杀手?”
拓跋茗打量了一下于白,“好端端的怎么问起战俘的事情了?你认识的人被勿黎军抓了?”
“你别管,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就成。”
“若是能动摇对方军心的重要人物,是会直接斩于马下用以示威的,若是小卒子,就不清楚了,每个营的处理方式不同,毕竟没人会关心小兵卒子的死活。”
于白双目赤红,“前段时间,最后一股突袭大祁边境的流军是属于哪支部队?驻扎在哪儿?”
拓跋茗盯着于白的双眼,摇了摇头,“那些事情向来是大哥独自吩咐的,我不清楚。”
于白也知道自己有点病急乱投医,拓跋茗再怎么样毕竟只是个公主,拓跋忽不会什么事情都告诉她。可是他想不出可以问谁,眼下他知道了云司易的失踪都急得跟没头苍蝇一般,他不敢想象若是云司简知道了会怎样。
即便云司简看似与云司易不亲厚,可于白知道他对自己的家人是多么看中,否则,又怎么可能违背着自己的心意不肯卸下云家人的责任。
“算了,当我没有问。”于白心不在焉地往回走。
拓跋茗喊住了他,“我可以帮你打听,但你要告诉我出事的是谁。”
于白看着拓跋茗,尽管从来到勿黎以来他什么事情都与拓跋茗商量,可这一次事关云司简,他不知道可不可以信她。
显然,拓跋茗大致有了猜测,可她偏作此一问,不知是在试探于白还是在确认其他。
两个人一个站在台阶上一个站在台阶下,都保持着沉默,之间的数级台阶似乎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具体是谁,我不能说,我只能说,是我很重要的人,十来岁,还,是个孩子。”于白吐字吐得艰难,拓跋茗的表情由失望变得苦涩。
“所以,不管我怎样,你都做不到完全信我是吗?”
“我只能说,我已经把我全心全意的信任给了一个人,无法再给第二个人了,这与你是谁怎么做都无关。”
拓跋茗勉强自己勾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至少,这句话你对我是诚实的。明天下午我给你答复,你别乱找人打听,大哥疑心很重,万一被他嗅到了不同寻常,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于白点了点头转身欲走,却又回过头,直视着还未回屋的拓跋茗,“谢谢。”
拓跋茗撇开视线,“快滚,我要睡觉了。”
第二日,拓跋茗如约去了于白住处,“是大哥的亲兵,暂时驻扎在离王城一百公里外的荒地,他们应该还是去替大哥抢粮的,至于有没有战俘,我没能问得出来。”
“多谢!能知道这么多已经很好了。”确实,昨日虽然急吼吼地去找了拓跋茗,但冷静过后,于白真的没对拓跋茗能打听到抱有太大希望,现在能知晓这些已经在于白的意料之外了,“若我想离开王城数日,有什么比较好的借口?”
拓跋茗与邵时同时叫了起来,“你想去驻地?不行!”
完全不理会两个人的一致反对,于白说得斩钉截铁,“你们不要跟我分析利弊,我听不进去也不想听。我就告诉你们我非去不可!你们不帮我我自己想办法去,你们帮我,那就想个万全之策我再去。”
邵时一脸纠结地看着于白,拓跋茗则是烦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于白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梗着脖子不说话。
等两个人都对于白的不按常理出牌镇定下来后,拓跋茗问道,“你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于白摇了摇头,“装病行吗?”
“不行。”拓跋茗一口否决,“若你真的要去,且不说一来一回路上的时间,单就你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就不好说,这期间你一直拒绝任何人往来,即便有我给你打掩护,也风险太大,而且,你要去就得出王城,没有邵时,你恐怕很难避开大哥三哥的耳目。”
邵时顺着拓跋茗的话道,“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能想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让于白跟我一起正大光明地离开王城,之后再行动就方便得多了。”
于白头疼地直挠头,“早知道现在想出个王城这么难,当初干嘛要费尽心思地进来。”突然于白灵机一动,“诶?既然我们都装神弄鬼糊弄这么多次了,要不干脆再来一次?”
“次数多了就容易有破绽了。”拓跋茗仍是不同意。